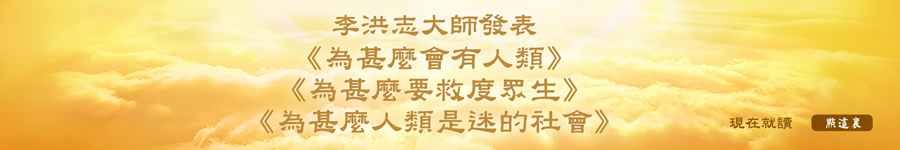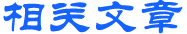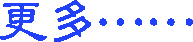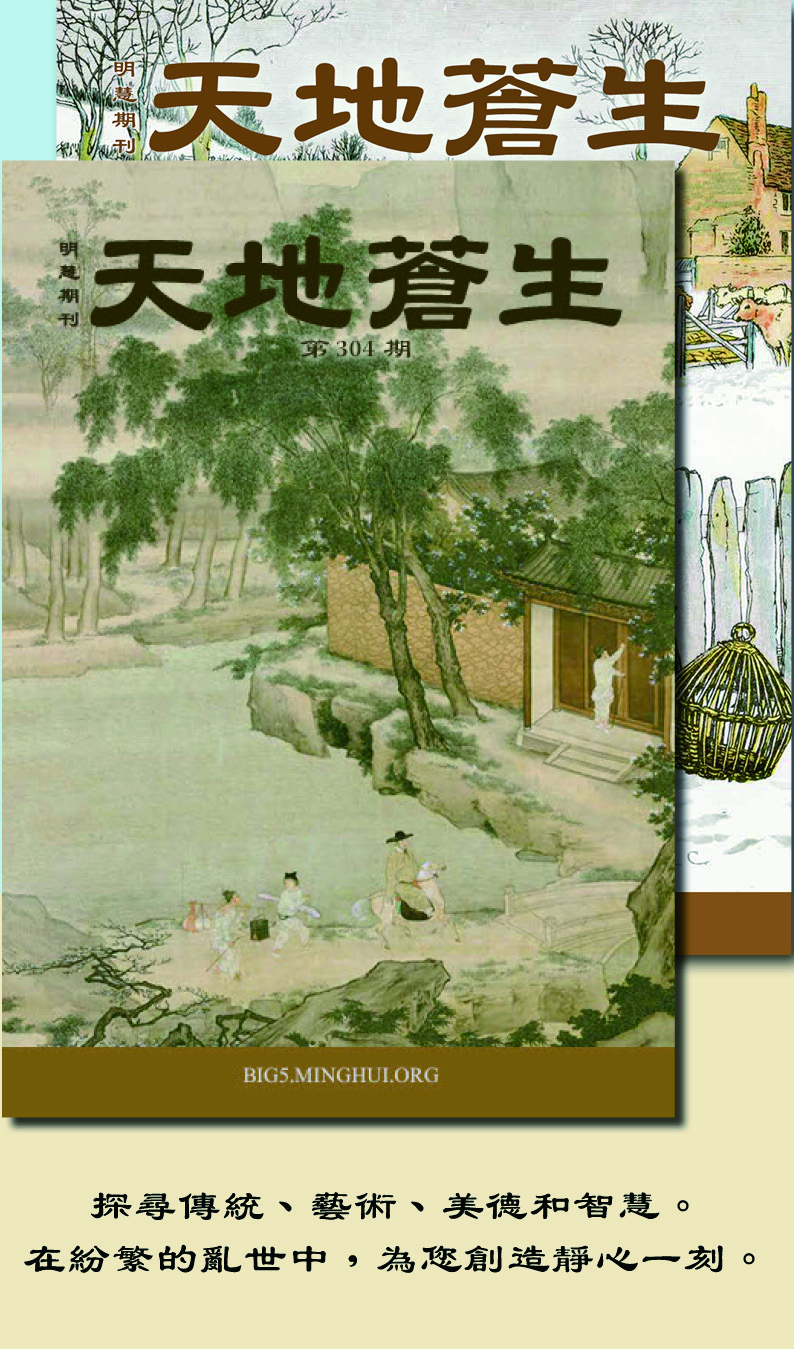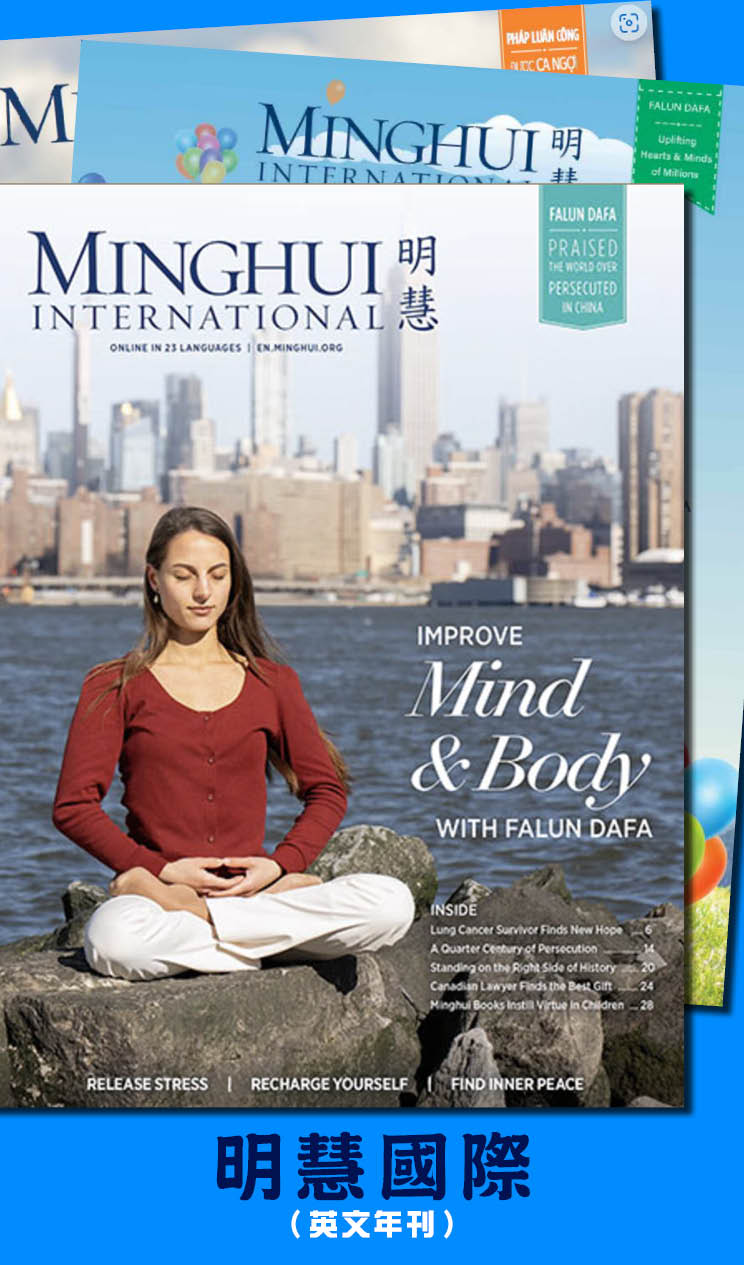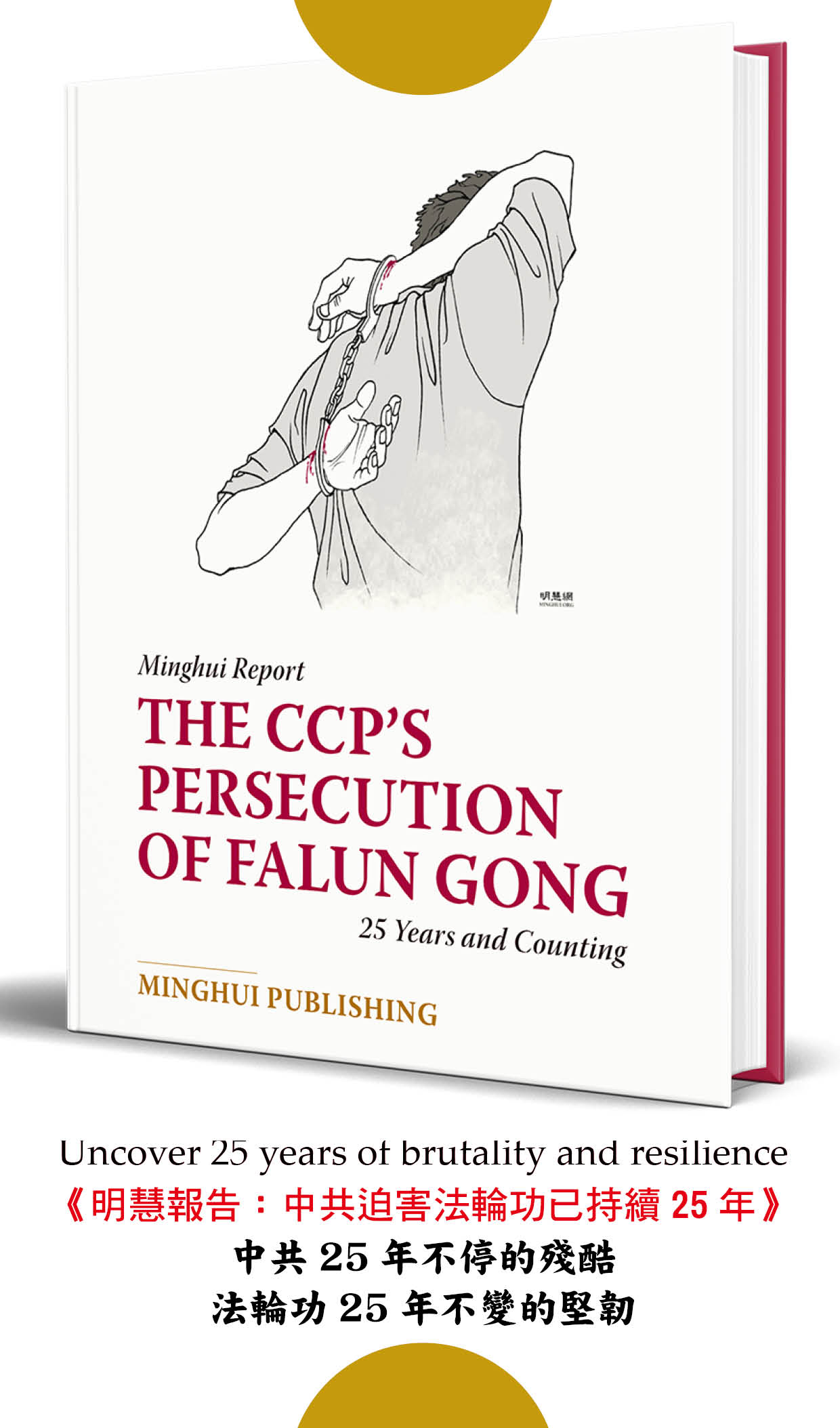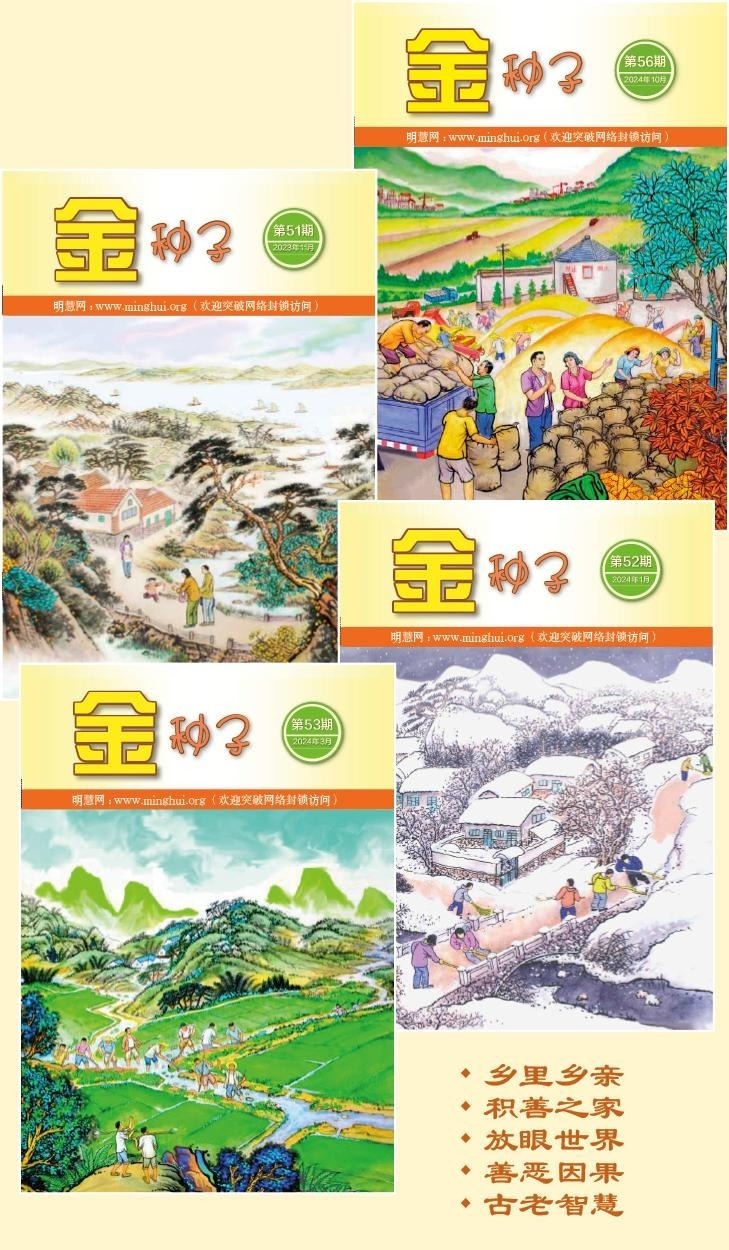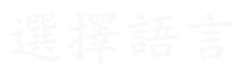明慧汇编:谎言欺骗掩不住 累累罪恶必昭彰(北京专辑2)
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披露在团河劳教所受迫害经历(一)
文/大陆大法弟子 龚成喜
(明慧网2004年1月30日)编注:大法弟子龚成喜(男),25岁,原为中国政法大学昌平分院行政管理专业大四学生,原籍新疆乌鲁木齐市。在校期间曾担任班长职务,是正直善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迫害中遭学校除名。
龚成喜于2000年底在北京散发真相传单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曾两次被送进“集训队”迫害,一次被无理延期10个月。在长达两年的迫害中,恶警使用了各种野蛮手段,比如罚站、罚蹲、电棍电击、强行灌食、不让睡觉等种种酷刑妄图逼迫他背叛信仰。作为所里的被“攻坚”(重点洗脑)对象,两年中他饱受了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不动摇,是被北京团河劳教所劫持的最坚定的大法弟子之一。
2003年龚成喜堂堂正正走出北京团河劳教所;同年8月不幸被邪恶钻空子,再度被绑架,到现在为止一直下落不明。
希望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关注龚成喜的遭遇,积极揭露迫害、予以营救。
我从小体弱多病,青少年时代饱受了病痛和绝望的身心煎熬,比同龄人更深地体味到了活着的艰辛,精神压力很大,在忧郁无助中没有了生活的信心。 98年我接触到法轮大法(法轮功)并很快开始修炼实践,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就收到了令人兴奋的奇效:病痛感消失了,整个人从灵魂深处脱胎换骨,逐渐变得健康、乐观。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为人处事,使我在学业、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得到了老师同学及亲朋好友们的普遍称赞。
法轮功给我这样的青年带来的是好好活着的勇气与希望,使亲朋好友们不再因我的痛苦而痛苦,同时给了我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优秀条件。
然而,99年4.25后,我却受到校方不准向他人介绍法轮功、撤销班长等学生干部职务、选择修炼还是上学等无理威胁,给我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带来许多麻烦。
99年7.20后,我们这些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大量守法公民,在一夜之间被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欲将我们“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使无数法轮功修炼者的生存条件面临极大危机,使多少无辜的家庭家破人亡。
99年暑期过后,校团委将我父母从新疆叫到北京,以中断学业要挟二老逼迫本人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在种种毫无道理的迫害和冤屈下,我选择了向政府请愿、上访,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造谣和镇压,还给我们炼功的合法权利。
1999年10月底我在向政府上访的途中被便衣抓到了天安门分局,在审讯室内,警察强行给我戴上下背铐、罚站马步、用胶皮棒猛抽我的臀部……使我在剧痛中汗流如雨,手铐嵌进了肉里。当晚,我被校方接回后,系党委、校团委对我施以高压,禁止我继续行使公民上访、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合法权利。为能够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被迫于第二天晚上流离失所,一个月后回校,被逼休学一年,由父亲接回家乡。
由于江政权在全国范围内搞恐怖的消灭法轮功运动,家乡的炼功人也被判刑劳教、电话监听、人人表态过关、株连亲属等等,家人十分恐惧,只好将我送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亲戚家躲避。但在那里,环境也十分紧张,到处抓人,亲戚们整日提心吊胆。
2000年7月22日,我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警察连拖带打地推上了警车,并在警车内揪着我的头发施暴。后来,我和其他上百名炼功人被押到另外一个公安局,凶恶的警察强迫我们每个人照相,手掌摁手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每个法轮功修炼者记录在案,以便采用各种方式使所有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无法上学、无法工作、无法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被非法关入拘留所、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遭受酷刑、强体力劳动及精神折磨,失去生存条件,从而迫使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那一次在公安局我被非法关押了48小时,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手续。并且被罚站连续好几小时,直到近乎瘫倒。晚上被扔进没有床的小号内,不准睡觉,更不准炼功,否则就要被毒打。
2000年9月休学期满由父母送回校,校方因我“复学申请”中“认为和平上访没罪”不合“要求”而迟迟不予复学。以致本人遭到父亲的棍棒毒打,好端端的家庭被无法无天的迫害正义良知整得鸡犬不宁。父母自知无力向江泽民讲理,为了图自家的一时安逸,就把所有冤恨撒在我的身上,逼我出卖自己的良心。这种悲剧在7.20之后的中国大陆是屡见不鲜的。在残酷的系统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下,无数的家庭破裂,无数人流离失所。
2000年10月,我陪同父母去天安门广场游玩,在我们一家上天安门城楼前,警察逼父母辱骂法轮功才准上城楼。
2000年12月20日,本人在北京大学分校和平散发法轮功真相材料时,被分校七八个保卫人员发现并当众殴打后送北京昌平公安分局看守所拘留。刚到看守所的头两天,我的一条腿便被犯人打得淤肿,一个多月不能正常走路。同号的另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经常被扒光衣服,变态的数名犯人竟将牙刷捅进他的肛门寻开心,并经常对他用各种变态流氓方式进行凌辱。
在非法拘留、白天被罚长时间坐板、晚上冻得无法入睡、一个多月不准洗漱、每天吃拉得咽喉生疼的窝头等不公正对待下,我开始绝食表示抗议,三天后,警察对我强行灌食。他们派犯人将我反架着胳膊硬拖了几十米,使我的胳膊几乎被弄折,鞋也拖掉了,直到寒风刺骨的门口被摁倒在地,由一名警察边骂“插死你”边使劲往我鼻孔里插橡皮管,强行注射进一碗水冲奶粉或玉米糊,完后快速扯出橡皮管,使我的鼻膜受到很大刺激。没有任何消毒设施和必要护理、甚至连犯人都可以帮助灌食。有一次,同号的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绝食被摁在地上插管时抗议:“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警察穿着皮鞋照他的头猛踢,导致眉骨处长时间瘀血……
在那里,我们被野蛮剥夺了和平抗议的最后方式——绝食,而遭受了更大的灌食摧残。十几天下来,见过我的人都说我已严重脱相,那时除了呼吸外,我几乎已没有力气,身体极度虚弱。而这一切,相信警察通过监控器看得是清清楚楚,但我仍每天被罚长时间坐板,晚上睡在寒风阵阵的靠门口的水泥地上,伸不开腿,翻不了身。
(待续)
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披露在团河劳教所受迫害经历(二)
文/大陆大法弟子 龚成喜
(明慧网2004年1月31日)编注:大法弟子龚成喜(男),25岁,原为中国政法大学昌平分院行政管理专业大四学生,原籍新疆乌鲁木齐市。在校期间曾担任班长等职务,是正直善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迫害中遭学校除名。
龚成喜于2000年底在北京散发真相传单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曾两次被送进“集训队”迫害,一次被无理延期10个月。在长达两年的迫害中,恶警使用了各种野蛮手段,比如罚站、罚蹲、电棍电击、强行灌食、不让睡觉等种种酷刑妄图逼迫他背叛信仰。作为所里的被“攻坚”(重点洗脑)对象,两年中他饱受了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不动摇,是被北京团河劳教所劫持的最坚定的大法弟子之一。
2003年龚成喜堂堂正正走出北京团河劳教所;同年8月不幸被邪恶钻空子,再度被绑架,到现在为止一直下落不明。
希望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关注龚成喜的遭遇,积极揭露迫害、予以营救。
(接上文)2001年1月22日未经任何审判质证程序,我被一女警察宣布判劳教一年,我问她判我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她支支吾吾说你自己查去,我就拒绝在劳教通知书上签字。
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月23日(除夕)凌晨,昌平看守所将我和另外四名法轮功修炼者铐上警车,押至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大兴区团河劳教所附近)。刚进调遣处的大铁门,一、二十名腰挎警棍、手铐,手拿七、八十厘米长噼啪作响的电棍的警察站两排将我们夹在中间。一人厉声称我们为某教,并强令我们服从命令,逼迫学员:从今以后站立、行走不许抬头,必须低头看脚尖,两手放于腹前;蹲(用于点名、等候吃饭、跟警察谈话等)要双手手指交叉抱后脑勺下蹲,两肘放于两大腿里侧,头扎到裤裆里,绝不许抬头,(被警察叫去时,首先要高喊:队长好。然后在警察面前这样蹲着。否则就是抗拒改造,要被电击)。走要碎步走直角。如果有人稍敢不从,这群恶警便上来疯狂电击、踹打学员。男女学员分开后,恶警逼学员念规范,并强迫写“在劳教所期间不炼功不传功不绝食不自伤自残”的保证书,每位学员都被强制写,不写就电,打骂,摁着手写……
我被分到二中队二班,每名法轮功学员都被警察指派一至二名“包夹”(即由非法轮功人员的劳教者充当),不许我们相互说话,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刚去的几天,我们被强迫每天从早到晚户外练队,三九严寒,一站就是几小时,还得高喊侮辱人格的“报告词”(每天吃饭前要喊报告词、回答警察问话要先喊报告词、练队要喊报告词,睡觉前还要喊报告词),强迫唱改造歌,遇着警察必须抬头高喊:队长好,然后立刻低头。打饭、上完厕所甚至被警察辱骂电击后必须高喊:谢谢队长。到了晚上强迫我们背劳教规范,背不会每天深夜12点多才让睡。
几天后,开始要我们劳动。即徒手往木制的一次性筷子头上裹一层纸,纸上印着“已消毒”,事实上极不卫生,患有传染性肝炎、性病的劳教人员都必须干,干活前从不让洗手,一屋40人左右挤得满满的,筷子堆得地上、床上到处都是,满屋子木头屑。(调遣处卫生状况极差,如:每天早、晚洗漱大便时间只有几分钟,常常刚蹲下就被警察叫骂着出去排队;长期不让我们去洗澡,直到发现大量劳教人员身上都是虱子,才让洗了一次澡,而那次也是将几十人一起哄进只有一两个水龙头可用的澡堂洗了几分钟;2002年夏,调遣处爆发流行性肝炎;……)
调遣处为最大限度的从劳教人员身上榨取利益,已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我们包筷子的规定任务是每人每天7500根至10000多根,从早晨6点起床开始不停地干到夜里12点还完不成,除了难以忍受的腰酸背痛之外,还要受到警察、普教的辱骂、殴打。在调遣处的一个多月,几乎天天如此。班里几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刀万辉、杨巨海、李学良、陈经建、贾林等因眼花、手脚动作已快到极限但仍完不成任务被队长强令到滴水成冰的户外坐在水泥地上干活达数小时,还完不成就剥夺他们的睡眠时间,通常只让睡三、四个小时。
法轮功学员徐化全(外语翻译,硕士,30岁左右,在分局被警察灭绝人性地用烟头烫掉一个乳头)因拒绝超时超体力的迫害性劳动,被二中队周中队长用三根电棍电击后,又24小时全身捆绑在床板上,命令包夹不让他睡觉,以逼写检查。看守徐化全的普教被特许吃小灶,加上队长背后撑腰,便肆无忌惮地辱骂、折腾徐。为了不让徐合眼,普教用橡皮筋猛弹他的眼睛、面部,令他痛苦不堪。我据理质问周中队长为何不让人睡觉时,周反倒说我在“对抗政府”。
同时,我们还被调遣处强制洗脑,调遣处于2月在大批队长的电棍包围下,强迫几百名法轮功学员集体观看给法轮功造谣的录像,并要求写认识。天安门自焚事件在《焦点访谈》播出后,我们除每晚被强行组织观看外,还要写认识。
2001年3月1日,我被从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押至北京市团河劳教所二大队。团河劳教所的主要任务是使被抓进去的法轮功学员转化(即通过长期高强度强制洗脑、精神强奸,用不让睡觉、电棍、毒打、体罚、精神刺激等手段强行使学员改变信仰,写出辱骂法轮功和拥护XX党的“四书”,并被劳教所逐一录念转化书的像,人为地把XX党和法轮功对立起来)。
同时在国内、国际社会上给法轮功进一步造谣、给镇压有理制造卑劣的借口。在警察蒋文来、倪振雄、王华等的唆使下,对我等不放弃法轮功的修炼者,除每天至少坐18个小时的儿童椅、被疯狂洗脑、中午不准和其他犯人一样睡觉、晚上比正常睡眠时间晚4个小时即凌晨2点左右才能休息(早6点之前起床)外,还对我们每人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熬夜,晚上最多时只能睡半小时,通常是整宿不让合眼,刚一打盹就被轮流值班的犯人推醒。那段时间我被折磨得几乎精神崩溃,骨瘦如柴。
犯人们在队长的授意下,可随意串班,残酷毒打体罚虐待污辱不放弃修炼者。我在班里被施以高压强制罚蹲数天,每天连续蹲18个小时以上,不准坐、起、挪动,仅有的两三次上厕所时间还要打报告,要看看管犯人的脸色。当然,这一切若不是警察支使,他们是不敢干的,因为按劳教规定这样做会被警察肆意延期。
几天后我痛苦万分,腿脚严重肿胀,鞋早已穿不进去,已不能行走。警察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刺激我。在班里,几个犯人围着我念栽赃法轮功的劳教所内部材料进行洗脑,我捂耳朵不听,说这是造谣,他们一群犯人便强行抓住我的胳膊,按住我,逼着我听。(有一次撅我的手指,差点就折了)。我奋力挣脱,他们就使猛劲抽了我十余个嘴巴(他们曾因我驳斥谣言而抽得我嘴角流血),并用掌疯了似的拍我的头;又一犯人抓着我的头就往墙上撞;另有犯人使重拳猛击我下巴,打得瘀紫……这种为强制法轮功修炼者接受洗脑的赤裸裸的暴力在队里时有发生,而值班的警察们个个不闻不问。
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整个160余人住的筒道刷厕所、扫垃圾等脏累活全是他们几个的。警察倪振雄说这是因为“没改造好” ──他们要把所有信仰真善忍的人改造成背叛信仰、出卖同修、出卖师父的人。如果我们不从,他们就对我们百般虐待和折磨,还说出种种这样无耻的借口。
二队警察王华常利用自己值夜班的时间找我谈话,凌晨3点半才让我睡一两个小时。在其纵容下,六班犯人常当着他的面体罚、威胁我。2001年4月,我调至五班,犯人李某积极“帮教”强迫熬夜,常对我动手动脚,当面恶毒攻击法轮功以刺激我,并无故辱骂我,我向王华反映,王华反而纵容、唆使迫害。2001年5月,二大队每天给全队人员上课,内容为由警察念栽赃法轮功的材料。我拒绝参加并绝食抗议,王华故意让一天未进食的我外出干体力活,并写材料给我造谣,说我抗拒改造。2001年6月,我被非法24小时捆绑在集训队期间,王华亲临现场,示意看着我的普教要进一步施暴。这是后来这名普教告诉我的。
(待续)
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披露在团河劳教所受迫害经历(三)
文/大陆大法弟子 龚成喜
(明慧网2004年2月1日)编注:大法弟子龚成喜(男),25岁,原为中国政法大学昌平分院行政管理专业大四学生,原籍新疆乌鲁木齐市。在校期间曾担任班长等职务,是正直善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迫害中遭学校除名。
龚成喜于2000年底在北京散发真相传单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曾两次被送进“集训队”迫害,一次被无理延期10个月。在长达两年的迫害中,恶警使用了各种野蛮手段,比如罚站、罚蹲、电棍电击、强行灌食、不让睡觉等种种酷刑妄图逼迫他背叛信仰。作为所里的被“攻坚”(重点洗脑)对象,两年中他饱受了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不动摇,是被北京团河劳教所劫持的最坚定的大法弟子之一。
2003年龚成喜堂堂正正走出北京团河劳教所;同年8月不幸被邪恶钻空子,再度被绑架,到现在为止一直下落不明。
希望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关注龚成喜的遭遇,积极揭露迫害、予以营救。
(接上文)2001年4月,有外国记者要来团河劳教所参观,全所上下开始统一行骗:每班都必须反复收看团河内部制作的录像:答外国记者60问,强令学员统一口径,欺骗媒体,其赤裸裸的瞎话令人咋舌。如问到这儿是否打骂虐待劳教人员,必须答没有;法轮功人员不准说是因炼功被抓,必须说是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劳教;问到这儿吃得怎么样,要答每月每人多少面、油、肉、菜……纯是骗外国人的鬼话。除此之外,每名未转化学员均被威胁不准“胡说”,否则“后果自负”。
警察倪振雄开会扬言:若有记者问话,不能说在看守所挨过打,更不准说有调遣处这个地方。
当天,记者到了东楼一层的三队,而三队早已将不转化人员和不理想人员几十人转至集训队北边的平房,因此采访人员看到的只能是事先安排的演戏了。每当有外界参观采访时,劳教人员的伙食就变好一天,而且当天取消例行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公开体罚,代之以打球。参观的刚出大门,马上又开始体罚。
顺便一提,团河劳教所欺骗外界参观采访的手段是层出不穷但又非常卑劣的。比如,投入大量资金改观劳教所的硬件设施以掩饰实质的疯狂践踏坚持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基本人权的罪恶。为了向外界粉饰其“文明”,近期有“劳教人员分级处遇”的措施出台,将劳教人员分为五个级别,最高级别甚至被许诺早餐牛奶鸡蛋、午餐一荤一素,可试工、试农、试学,周末放假。事实上,能享受这种尚未实行的、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的待遇的劳教人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所有不转化的法轮功修炼者均被划为最低的一级,属严管,仍得被高压洗脑、熬夜体罚、送集训队、关小号、捆绑、吃窝头、不准采买食品甚至日用品等等。而这些残酷折磨却被新的措施巧妙地掩盖了。
迫害场所集训队、攻坚楼向来是不对外开放的,而所有敢说真话的法轮功修炼者从来不让参观人员采访到。因此,官方的报导纯粹是欺骗。对拒绝放弃法轮功的人员来说,团河劳教所就是“人间地狱”。
2001年5月27日,为抗议丧心病狂的洗脑和长期不准睡眠,我再度绝食,在没有得到警察任何回复的情况下,于当天下午被倪振雄、赵队长强行架到集训队进一步迫害。
集训队是一个全封闭式的独院,里面阴森恐怖,专门酷刑迫害坚定信念的法轮功修炼者。其令人发指的暴行别说外界记者、参观者绝不准入内采访,就是劳教所的警察未经允许也不能进入。这里面用铁笼子关押人。每天24小时都有十几名劳教人员值班。里面的人就象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相互间都不允许说话,没有任何的自由。劫持我去的当天,一名叫李代义的嫖娼犯人当着集训队大队长、护卫队大队长兼管理科科长刘金彪和管理科科长任宝林的面猛抓我的下身,使我痛苦不堪,而刘和任不但视而不见,且命令犯人用多根带子将我全身24小时牢牢捆绑在床板上,(连续捆绑了一个月,《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连续使用戒具不得超过7天)塞进闷热狭窄的禁闭小号里。小号长2米左右,宽1.5米左右,整天不见天日,不准起身洗漱、更不准洗澡,连小便都只给解开上身绳坐着进行,便完马上捆绑,时值天气炎热,除了饱受不能翻身、内脏挤压、绝食绝水、死一般的寂寞的巨大痛苦外,我的身上还长满了痱毒,后背、臀部已开始溃烂。在这种情况下,每天还要被如死囚一般五花大绑强行拖出去用橡皮管从鼻孔插到胃里灌食,每次皮管插到鼻粘膜处,我都痛苦得泪如雨下。而犯人李代义常当着警察的面恶意将已插入我胃里的皮管来回抽,使我剧烈呕吐,几近窒息。五六天后,我的一个鼻孔内就因粘膜处被反复插管刺激而严重肿胀了。同被捆绑的法轮功修炼者武军,因抗议劳教所非法延期半年而绝食。在警察刘金彪的唆使下,普教李代义、宋万军、李鹏等每天早上4点将武军拖出屋,用绳子绑住他的胳膊拉拽着猛跑,武军不跑,被他们毒打得浑身青紫。当武军要求上医院验身时,刘金彪公然说:“你皮肉嫩,一碰就黑”。在警察的纵容唆使下,普教经常不准武军上厕所,普教李鹏给绑在床板上的武军“拿麻”(长时间按住大脖筋,一会儿人便会休克),导致武军不省人事;他曾使猛劲将武军一个耳光抽倒在地,并以此为乐……从2001年5月至7月,武军被连续活活捆绑了三个月!仅仅因为他不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
(待续)
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披露在团河劳教所受迫害经历(四)
文/大陆大法弟子 龚成喜
(明慧网2004年2月2日)编注:大法弟子龚成喜(男),25岁,原为中国政法大学昌平分院行政管理专业大四学生,原籍新疆乌鲁木齐市。在校期间曾担任班长等职务,是正直善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迫害中遭学校除名。
龚成喜于2000年底在北京散发真相传单被绑架到臭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曾两次被送进“集训队”迫害,一次被无理延期10个月。在长达两年的迫害中,恶警使用了各种野蛮手段,比如罚站、罚蹲、电棍电击、强行灌食、不让睡觉等种种酷刑妄图逼迫他背叛信仰。作为所里的被“攻坚”(重点洗脑)对象,两年中他饱受了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而不动摇,是被北京团河劳教所劫持的最坚定的大法弟子之一。
2003年龚成喜堂堂正正走出北京团河劳教所;同年8月不幸被邪恶钻空子,再度被绑架,到现在为止一直下落不明。
希望大法弟子和国际社会关注龚成喜的遭遇,积极揭露迫害、予以营救。
在武军和我绝食期间,北京市劳教局管理处的某处长曾来视察并怒斥我。没两天,团河劳教所、调遣处便合伙对我们采用了灭绝人性的填鸭灌食。大概是在6月10日这天,犯人们架着我来到集训队一间阴森恐怖的小屋里,从调遣处专门来了一个姓申的警察带着一个膀粗腰圆的犯人,屋里已有包括团河的庄许洪副所长、警察刘金彪、警医肖政在内的五六名警察和好几名犯人(李代义等)在床边围了一圈。当时几名犯人将我抬到床上摁住,用绳子死死地捆在床上,由几个人分别按着我的腿、胳膊和胸部。肖政用听诊器听听我的心脏说:“没事”。然后有人捏住了我的鼻子使我不能呼吸,那个膀粗腰圆的犯人用两拳猛顶、钻我的两腮,逼我张嘴,另有人开始拿钢勺撬牙,剧痛和几近窒息中,我感到血腥味充满了口内,非常的痛苦。牙撬开一点缝,他们立即将钢勺捅进嘴里抵住上下牙开始往嘴里灌流质,并将嘴捂上。由于我挣扎着呼吸,流质马上憋进气管,鼻子又被捏住,我当时感觉已快窒息且神志不清,只看见一个个面目狰狞的脑袋凑在眼前……当天下午,刘金彪令犯人将我架到小院又用此兽行对我灌了一次,当时所教育科还来了一名警察用摄像机录下了灌食全过程。灌完食,我的两腮被顶得严重充血肿胀达一个多月。刘金彪对此解释说这种灌食方法很科学,新安劳教所灌了几个老太太都没事。
在被野蛮灌食前后,我问所长庄许洪为什么对于二大队打人的事不和我谈就灌食?为什么不让人炼功?为什么用这种残忍方式灌食?他说,没什么可谈的,这是对你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并强令我写保证,我不答应。两三天后的一个白天,被刘金彪派来看着我的普教宋万军、徐铮、王争、黄潆涛等突然关上门窗,对全身捆绑在床板上的我施暴:他们无故对着我辱骂法轮功,写辱骂法轮功的纸条往我的身上、臀后塞,羞辱我,刺激我。并由几个人摁住我被捆的手写“保证书”,我大声喊叫着不写,惊动了一名叫徐建华的集训队警察推门进来。我请他以警察的身份制止犯人施暴,而徐看到了施暴场面却说:我和你又不认识,你冲我嚷什么。(事实上,他一直主抓管教工作)说完扬长而去。宋万军等普教顿时变本加厉,关严门窗,用圆珠笔在我身上脚上写辱骂法轮功的脏话,并用圆珠笔尖猛杵我的脚心、虎口,将我的手指涂满只有警察办公室才有的印泥强摁在侮辱纸条上……折腾了几个小时。当天或者是第二天晚上,一名叫张建林的普教被调过来值班,他一进门就高声骂娘、冲过来猛抽我的耳光,说我让他又值上班了(事实上,普教们十分愿意值班,因为值班可加分、提前解除。特别是干得让警察满意的),并疯了似的用重拳猛击我的下颏,拧我的脑袋。以后的几天,他们几乎天天凌辱、殴打全身捆绑在床板上的我。甚至每次必撕烂我的外裤、内裤流氓侮辱……因天气炎热又长期不准我起身洗澡,在他们撕烂内裤施暴后,身上的异味招来群群苍蝇在我的小便头上叮爬,他们却视而不管。在身心极度痛苦的这些天中,我曾问刘金彪为什么往我身上贴污辱性纸条、写辱骂法轮功的脏话,他回答说:这种方式不是集训队发明的,别的劳教所早就有。在被连续捆绑的过程中,虽因前段绝食和整日被捆人已虚弱消瘦不堪,但每天却只许我吃窝头、咸菜,不让正常采买食品和洗漱用品、手纸等;除此之外,还经常剥夺我的睡眠时间,强迫我听诽谤法轮功的造谣材料。这些,就是团河劳教所的“为你们好”、“革命的人道主义”。
2001年9月4日,是我禁闭10天、集训三个月的记大过处分(只因绝食抗议不让法轮功修炼者正常睡眠,殴打、体罚、辱骂法轮功修炼者和要求炼功)到期的日子。当天,刘金彪要我写一份“集训总结”,我便写了:普教宋万军等人对我一再实施暴力时所使用的印泥、法轮功创始人画章等都只有在队长办公室甚至教育科才有,不知凭他们的劳教人员身份是如何拿到这些“违禁品”的?刘金彪看后恼羞成怒,立即将“总结”撕了,叫我“滚蛋”,并威胁说:“你要是不想走,延长你的集训期还不是填张表的事!”
2001年7月底至9月初,我被关押在集训室的铁笼子里,在那里,我和其他三名法轮功修炼者每天被强迫抱膝坐板(连盘腿坐着都不许),除了吃饭上厕所外,从早晨起床坐到晚上睡觉。每天吃难以下咽的窝头咸菜或没有一点油花的熬菜,喝生水,时常被拉到警察办公室强迫洗脑、观看给法轮功造谣的录像,还要写认识,经常因拒绝转化而被警察吼叫怒骂或暴力威胁。压力巨大。在这期间,家里给我邮来一封家信。按照中国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52条的规定,“劳动教养人员的通信,不检查。会见家属时,不旁听”。但是集训队警察刘金彪、徐建华、张宜军不但私拆我的家信,而且扬言要开一个全队大会,当众念信。对于有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消息,劳教所在上级授意下,不惜践踏相关法律法规,全面封锁。如普遍开拆、检阅法轮功学员的私信,监听每位法轮功学员同家属的电话;将法轮功学员手中的法轮功材料,有关于宗教、信仰、预言等方面的书和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留的通讯录、法轮功学员的日记等一律视为“违禁品”,每隔几天便有护卫队警察“清监”,一经查出,轻则没收,重则延长劳教期、送集训队迫害。警察在搜身时,好几次都要求我当众脱下内裤。
刘金彪、张宜军等警察常把我单独找到办公室给我洗脑施压,逼我抄污蔑法轮功的造谣材料;威胁我说:“电熟了你丫的”。有一次,一名警察手拿电棍逼我们在烈日下长时间一动不动站立,我支持不住晕倒在地,他在一旁嘲笑羞辱法轮功,而普教李代义当着其面恶意将水洒了我一身。警察全然不顾我们的信仰自由和肉体承受,一味施加恐怖的压力,野蛮践踏法律和基本人权来逼迫我们放弃,以完成所谓的“转化任务”,拿到高额奖金。据悉,警察转化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不仅会得到千元的专项奖金(几乎相当于其一个月的薪水),还能得到升迁的政治资本。有一次,我被警察叫到办公室训斥,恰好管财务的一名年轻女警察在场,集训队的一名男警察问她:“怎么还不发奖金啊?”她露骨地说:“那你们赶紧转化(法轮功)啊!”
在团河劳教所,警察利用普教来虐待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是非常普遍的。如果普教做了警察想做却碍于身份不大好公开做的事,且达到了警察的目的,那一定会被许诺提前好几个月解教。反之,若哪个法轮功修炼者炼功、甚至说话,值班的普教就会遭到训斥,甚至更惨。比如普教李代义,此人因嫖娼被劳教3年。劳教期自1999年7月至2002年7月。从他入所以来,积极参与毒打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邀功请赏,用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可谓残酷至极的“整江姐”的手段迫害了不知多少名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从法轮功班的班长到集训队值班大班长,到最后被减期半年释放,无不是踏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巨大痛苦换来的。据我所知,他用绳子捆绑过不知多少名学员,拿铁锁砸法轮功学员杨树强的头,打伤法轮功修炼者刘兴杜的胸部,用膝盖撞伤我的肋部,等等暴行,都是在警察的暗中支使下出台的。在劳教所里这样无法无天,按规定早该延期一年,可李代义却在充当邪恶打手中多次获“劳教所(局)嘉奖”而提前半年释放。正如一名曾对我施过毒手的普教后来告诉我的那样:没有队长(警察)发话,谁敢打啊?上次对你,队长对我们说:“干什么吃的,某某某是怎么转化的?(在残酷迫害中被迫转化的)”。所以我们才打。
2001年7月,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的交劳教所保管的贵重衣物被当时的集训队大队长刘金彪私自卖掉,有几千元的羊绒大衣等等。其中就有我的一件一百余元的休闲上衣。2001年10月,部分受害学员曾向副所长庄许洪公开提到此事,庄承诺,一周之内协调解决,结果到2002年12月19日我临走时,还没解决。
2001年9月至11月,我在七队、五队被不停地洗脑迫害。2001年11月4日,也就是临近我一年劳教期满的前一个半月,我被强行送进了团河“攻坚楼”。“攻坚楼”原为旧西楼,在2001年10月底新楼入住后变成了一座空楼,被专门用来强制转化法轮功修炼者。魏如潭、秦尉和我等6、7人于当天被强行劫持到“攻坚楼”一层(那些一直没转化并且快要到期的法轮功修炼者被关在一层迫害)。在阴森森的一层,有6、7间屋子,屋子里面只有一张放在地上的床板。我们被分别关在屋里,施以巨大压力强制洗脑。为了彻底摧毁我们的信念、不让我们互相见面和制造出彻底剥夺自由的高压恐怖环境,教育科韦科长和责任警察,将每间屋子门上的玻璃用报纸糊上,不准我们见面、朝外看,连上厕所都得分别去。整天坐在塑料儿童椅上被强迫谎言洗脑,早晚各由一名警察在屋里监管,不准随便站立、走动,更禁止出屋,不准有任何私自行动。洗漱上厕所有“包夹”步步紧跟,厕所、水房安有监控器。晚上睡觉每屋都有一名警察和一名犯人看着。由于环境高度封闭,其他劳教人员和外界根本无从知道这里的实情,来团河劳教所参观采访的外来人员是不能进集训队和攻坚楼的。洗脑只是手段,劳教所最终的目的是逼迫我们写出放弃、污蔑法轮功的书面材料并录像,用来欺骗其他法轮功修炼者和国内、国际媒体,粉饰根本不存在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所谓政策,掩盖暴力镇压的内幕。为此,在发现洗脑对我们不起作用时,就开始不让睡觉、体罚、殴打、电击。
有一次,一名违心转化的人偷偷告诉我前几天晚上好几个警察拿多根高压电棍电了魏如潭一宿,并警告他别说出去,魏让他看了腹、背上全是电伤。当天,魏被迫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下违心地写了转化书,并被警察强行作了念转化书的录像。同一天,教育科科长姜海权、王婷婷、二队队长刘兵(音)进了我的屋,问我感觉怎么样。我沉默,姜海权和刘兵便拧着我的胳膊,要往我身上写侮辱法轮功的脏话,我不从,刘兵便大骂“王八蛋”。
还有一次,警察岳清金无理恶意当面辱骂法轮功,我不接受,他便找借口冲上来用胳膊死死勒住我的脖子往后拖,使我喘不上气来,身上被他掐烂了好几处。
2001年12月16日是法轮功修炼者秦尉被延期半年到期的日子,此前的几天,秦尉突然毫无踪影。我心里十分明白他无法想象的艰难处境,那段时间,楼上在深夜经常传来令人惊心的拳打脚踢的声响和叫骂声。12月14日左右,一名“包夹”告诉我几个警察让秦尉在写东西,秦尉十分痛苦……在劳教所,警察们就是通过这一整套的无法无天的整人手段强奸人的精神信念,迫害人的肉体,达到逼迫法轮功修炼者写出书面转化材料、拍摄转化录像,哪怕是违心的,用以给更多的人洗脑,欺骗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待法轮功修炼者,中国的法律早已是一纸空文,没有渠道可以解决因修炼法轮功而惨遭迫害的冤案。那些至今仍在劳教所被关押的修炼者极其悲惨的处境大部分都不为人知。为了避免留下迫害证据,愚弄民众和舆论以维持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警察越来越隐蔽地实施迫害,如:他们在电击修炼者前将他牢牢捆在床板上,并用布蒙住他的眼睛,不让看到实施电击的警察;用布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喊出声,以免让人知道;绝不许有任何一个劳教人员在场;专门电击隐蔽部位等。因此,我所能了解到的迫害事实只不过是很少的一点。
2001年12月19日是我被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12月16日左右,所里的两名警察前来问我的一些情况,我保持沉默,后来警察尹某某问我到底转不转化,我说不转。他便开始故意找碴:刚才进门为什么不喊报告?背背《劳教人员守则》。其实我知道,只要我写了材料并录像,三天后便会被释放;如果不写,那就将被非法延长劳教期,而刚才的问话只不过是在凑延期的“证据”而已。警察尹某某常以“你们信仰有神,就别吃人饭、说人话、拉人屎”的流氓说法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这种不讲人权与信仰自由的无赖言论常被团河劳教所的警察作为对修炼者施加仇恨与暴力的荒诞借口。
当天晚上,警察刘国玺组织了一次集体学习,内容为轮流念给法轮功造谣的书,并要求我参加。事实上,第一,警察知道这种机械的洗脑对我已不起作用。第二,刘国玺不是我的责任队长,没必要让我参加念书,而当时那里面念书的人都不是来给我洗脑的。第三,开始念时,并未提到法轮功,因此我并未抗议,刘便迫不及待地让念攻击性的段落,等着我说不。待我提出反对时,刘竟出奇地平静,并马上让我到别屋。第四,等我去了对面的班,再也没有听见里面继续“学习”的念书声,后来在我被延期10个月的通知书上说到此事是抗拒学习教育,反改造。可见当时那只不过是给我挖的一个“陷阱”。而后来我得知在场的念书者均被要求作出关于我不参加学习、抗拒改造的证明。
团河劳教所中所有到期但是不放弃“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都被延期。延期的起因一般都是:坚持法轮功思想、绝食抗议残酷迫害、拒绝接受洗脑等。一次延期最少是半年。对于普通的劳教人员,这种延期只有在其逃跑或是犯新的大的法定的罪过时,而且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才出现的。而对于法轮功修炼者却可以随意的施加,不受任何的法律约束。比如,在我12月19日到期前三四天,警察就明确告诉我:写保证就能回家,不写就延期。2002年5月底,团河劳教所副所长李爱民在全体劳教人员大会上公开宣称:“不转化就别想离开劳教所!”而为打上“依法”的幌子行骗,延期的理由从早期赤裸裸的“不转化”变成了“抗拒改造”,其实本质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12月16日晚,刘国玺给我组织“集体学习”后的两三个小时,教育科廖科长拿着手铐和警察刘兵(音)将我又一次送进了集训队。当时集训队大队长刘金彪开铁门时问廖科长集训多长时间,廖随口说了一句:“一个月”便走了,根本没有必需的法定书面集训材料,可见当时的材料还没造完。事实上,那一次我被集训了整整三个月。
12月19日晚,我被5、6个普教架到集训队办公室。五大队姓张的副大队长和另一名警察向我宣读了延期10个月的决定,使我精神上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延期的原因为:1、坚持法轮功。2、2001年5月27日绝食抗议迫害。3、2001年12月16日抗拒读造谣材料的“学习”。宣布后,警察问我是否签字,我以沉默拒绝,集训队大队长刘金彪、警察徐建华便唆使普教将我架到禁闭室小号,那里面的床板上已准备了好几根捆绑的带子。刘金彪欲将我捆绑,我质问他:“我一没有过激的言论,二没有任何危险行为,凭什么捆我?”在一旁的徐建华却无理要求说:“你写不写保证?”刘金彪说:我这是为你安全。这时,普教李代义一脚把我绊倒摁在床板上对刘金彪说:“刘大,你甭管了。”说着便当着刘金彪的面和另外几名普教把我死死地捆在床板上。就这样,我再一次被24小时连续捆绑了半个月,不准采买、每天吃窝头咸菜,每天一次去厕所时,被普教像死囚或动物一样用两条绳子拴住肩,一边一人牵着,蹲大便时,将两条绳拴在水管上,严重侮辱我的人格尊严。而这些,都是集训队的警察指使的。
2001年12月23日左右,普教李代义在给我捆绑时,为泄私愤,对着躺在床板上的我用膝盖猛跪,导致我右腿、右胸痛了近一个月。当晚,劳教所的警医诊断为“软组织挫伤”,我问警察徐建华如何处理这个恶性事件,他竟说:你先把你的问题(写保证书)解决了再说,而且李代义也不会承认是他干的。后来,我将此事反映给教育科科长姜海权等警察,一直没有人管。可见,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真是政匪一家,警察在江氏的幕后操纵下,已成为暴力镇压的工具,不惜出卖职业道德、执法原则,鼓动犯人对法轮功修炼者犯罪,以逼迫放弃信念。而对法轮功出手狠毒的犯人常常会暗地里得到警察特殊的奖励,如减期、给犯人烟抽、打电话、盒饭等。事后,李代义流氓地对我说:“这张死人床,你还要躺两个月。”那意思是只要他2002年2月提前解除之前,是不会给我松绑的。犯人倒可以行使警察都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实施的制裁权力,可见集训队警匪串通的邪恶程度。此前,多名普教告诉我,李代义居然拿电棍电击某个劳教人员,并将其拖到小号打得喊“爷爷”。当天值班坐筒的警察却不闻不问。
另外,在集训队,按规定本应当给集训人员采买日用洗漱品,可那儿的警察却拿这个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作为逼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绝食、放弃修炼的要挟。在那里,任何私有的物品、权利都可以被警察任意剥夺,原因是坚持法轮功修炼。
大概是在2002年2、3月份左右,我看见攻坚楼的警察刘国玺来集训队取电棍,那一定又去电击某个不转化的法轮功修炼者了。
在集训队被关押了三个月后,我于2002年3月15日被送入了七大队。七大队是涉毒队,劳教所将我放到那里隔离。刚去七大队,我便听一班的劳教人员谈起了前几天的事。赵明(爱尔兰三圣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2000年5月13日被中国当局非法抓捕后,劫持到团河劳教所判劳教一年,因赵明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而惨遭酷刑折磨,并于2001年5月12日劳教期满时被无理延期10个月)在2002年3月12日期满释放的前几天,被逼迫配合当局的官方电视台作一个造谣的节目。当天,赵明同几名洗脑人员被搁在一班,和一班的几名普教一同被录像,内容有:三餐吃得很好,有鸡蛋、宫爆鸡丁等。(事实上,团河劳教所的伙食根本不怎么样,甚至很差。通常早餐是陈年的玉米熬的粥和发酸的馒头、咸菜,中午是跟中药一样的菜和馒头,晚上又是馒头咸菜粥,而对于不转化的法轮功修炼者每天只有半生不熟的硬窝头和咸菜)对赵明体贴照顾。(事实上,赵明因不转化常被体罚虐待,电棍电击,不让睡觉等等,这些都被当天的作戏掩盖了)这种对内镇压、对外行骗特别是同官方媒体共同欺骗民众与国际社会的手段在团河劳教所不断地上演。
2002年4月25日,五大队大队长杨保利来七队时,我向他询问到底给我做了哪些延期材料和延期的法律依据时,他只说:你自己知道。后来我以绝食请求他履行法定义务,告知我被延期的相关材料时,他才勉强答应晚上给我找来。谁知到了晚上,他带了两名警察气势汹汹地找到我说:你要绝食随便。最后什么问题也不给解决。
2002年8月27日,我写了一份递交给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的诉讼状,控告团河劳教所二大队警察蒋文来、倪振雄、王华于2001年3月1日至2001年5月27日对我实施的长期不让睡觉、纵容唆使其他劳教人员对我打骂、体罚、虐待、侮辱等执法犯法的非法行为。并将此诉讼状交由七队警察替我代转,但一直到今天,仍杳无音信。
2002年9月19日,我在七队透过窗户看见三大队的警察刘国玺等从早上6点开始又在操场上体罚魏如潭等三名法轮功修炼者,刘国玺要求魏等三人连续长时间做蹲起,直到他们站不起来了还不准停;强迫魏等三人趴在他面前无休止地做俯卧撑;还一刻也不准休息地让他们绕着操场跑个不停;警察刘国玺在迫害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时,常发出一阵阵变态的狂笑……一直折腾到中午。回队的时候,刘国玺发现我和另外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在窗户里看他,他怒不可遏地骂:“你他妈找死?”后来又冲到七队训斥我。
9月23日,我将警察刘国玺的非法行为整理成一份递交给团河驻检的检举信,交由七队警察代转,几天后,七队警察告诉我已将信按程序交给所管理科了。再后来,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来自任何有关部门的任何回复。2002年9月底10月初的一天,北京市劳教局管理处的一名处长(就是在2001年6月我绝食期间前来视察并怒斥我的劳教局警察)到七大队找我谈话,我向其反映了刘国玺执法犯法的行径,他却说上面虽然要求严格执法,但基层执行需要过程。为虐待法轮功修炼者、掩盖警察罪责寻找借口。后来,我又问他:为什么劳教到期不放人?他说:没转化的没改造好,会危害社会。我说:如果单从法律角度而言,怎么能在主观认为此人会危害社会而没有任何事实、行为的证据下就作出到期不放人的处理?而且外面610办公室办转化班(洗脑班),强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有没有法律依据?他说:实践证明,办班是一种有效的转化方式。照什么法律我不知道。我又问他:你也不知道依据什么法律?他重申:不知道。后来我又问他姓名,他说不能告诉我。在谈话中,他说已经知道了我写诉状和检举信的事,并明示我不转化将会被送洗脑班继续迫害。
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后某天,教育科科长张福潮找我谈话,我向他反映了写诉讼材料一事,他说:“你这不是给自己延期凑材料吗?”
2002年12月,在被警察绑架到集训队后,我认为自己在被非法关押的两年来,从毫无法律依据、未经任何审判及质证程序就被北京昌平公安分局无理判劳教一年,到2001年12月19日和2002年10月19日北京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未经任何对我的调查取证、正常审核的程序,任意强加给我两次非法延期(累计延期长达一年,加上被判劳教的一年,共被非法关押两年),而延期的理由又非常荒诞,是赤裸裸的对信仰“真善忍”的流氓惩罚,导致我两年失去了人身自由;从2001年1月23日至3月1日在如同纳粹集中营一般的北京市劳动教养人员调遣处,到2001年3月1日至2002年12月19在北京市团河劳教所,我仅仅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就受尽了高压洗脑、不让睡觉、长期隔离捆绑、插管撬牙的野蛮灌食、超时超体力劳动、非法超期关押、人身侮辱、体罚毒打、威胁恐吓、剥夺基本生活必需等等接连不断的精神、肉体的严重摧残,使我的身心所受伤害之大,是刻骨铭心、难以想象的。因此,当时我决定再次通过法律手段控诉凶犯们对我的基本人权、信仰自由的暴虐践踏。然而,结果依然是令人绝望。2002年12月16日,我将检举北京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北京市团河劳教所对我实施犯罪行为的三封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举信按劳教所规定交给了团河劳教所副所长李爱民。而2002年12月19日,我临解除之前,劳教所警察将我所有检举信、诉讼状的副本和所有私人的诉讼材料,以“劳教所规定”的荒谬借口,强行没收了。至今为止,我没有得到我的任何一份检举信或是诉讼状的任何回复。事实上,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许多法轮功修炼者的情况都可以证明:在中国大陆当前的环境下,连法律诉讼这样的基本方式都被禁止用来替法轮功修炼者维护起码的合法人身自由、信仰自由、不受酷刑虐待等基我权。更令人恐怖的是,当局会以用法律手段维护法轮功修炼者权益的合法行为作为进一步打击报复当事人的口实。比如:法轮功修炼者李春元于2000年底状告国家主席江泽民践踏法律迫害法轮功,2000年12月28日便被非法绑架,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劳教一年半。在团河劳教所,他又因写诉讼状控告警察对他的非法虐待而被关在集训队的铁笼子里已至少半年,整日被罚一个姿势坐板,不许出入,说话;每天吃干硬的窝头和咸菜。其检举信、诉讼状同样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任何回复。我的许多诉讼材料都在团河劳教所,相信当局会以此为证据,对我实施新一轮的恐怖行动。
2002年10月19日这天,是我延期10个月到期的日子。当天白天,警察告诉我说要放我回家。一直等到天黑,一名警察让我收拾东西并到队长办公室等候。不一会儿,教育科科长张福潮、龚伟,还有护卫队的几名警察来到办公室。护卫队的两名警察突然将我摁在椅子上不能起身,这时张福潮对我说:“由于你不转化,现决定给你延期两个月,送集训队执行。”这使我又一次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当时宣布的时候,连延期通知书都没有,就强行将我往门外拖。我当时呼喊:“你们凭什么给我延期?”几名护卫队警察怕其他人听见,便扒下我的眼镜,找来一块毛巾,死死地将我的嘴勒住,使我无法说话,并由几名警察拽着我的头和四肢往楼下拖,在夜色中一路勒着嘴抬到集训队。送到集训队后有人立即用胳膊卡住我的脖子将我往小号里弄,令我几乎窒息,后将我牢牢捆绑在已准备好床板的禁闭小号里。整个过程是无法无天、没有人性的恐怖流氓绑架!而实施者正是一向标榜“教育、感化、挽救”和“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对待劳教人员”的团河劳教所干警。
被强行隔离捆绑到狭小寒冷的小号后,我开始绝食绝水,五天后,被强行插管灌食。我再一次为抗议迫害而遭到了身心的极度痛苦。绝食被捆期间,劳教局副局长戴建海同团河劳教所副所长李爱民来集训队视察时走过小号,我呼喊“为什么给我非法延期?”他们不作任何回答。另一次,团河劳教所所长张京生来小号,我问他劳教所为什么体罚虐待法轮功修炼者,他当面撒谎说:“没有啊。”而我在东楼七队的四个月,几乎天天看见三大队警察刘国玺、白中银等、教育科科长杨金鹏、五大队警察张某某、杨斌等专门残酷体罚虐待不转化的法轮功修炼者,比如,强令修炼者绕操场跑圈,一跑整半天不准停,下午或第二天接着又是半天,累得几人迈不动步,几乎天天如此。“十一”的几天是中国大陆的法定节假日。而2002年“十一”放假的几天,其他队的劳教人员都停工、休息了,唯独户外五大队的警察杨斌强逼法轮功修炼者王方甫、刘力涛在大雨中不停地跑圈;强制不转化者“站军姿”,而且专挑夏天的黄昏在草丛边上站,故意让大量蚊虫叮咬却不准他们动一下,一站至少一小时;在操场上,还光天化日之下罚几名修炼者单腿跪在操场上,长时间不让起来、不准换腿;强迫修炼者背着手一圈一圈地绕操场蹲着走,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和肉体虐待;无休止地强制修炼者做“蹲起”,一做就成百上千不准停;2002年8月15日早晨出早操时,警察刘国玺在大操场当着劳教所几百名劳教人员和警察,对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猛扇耳光,并破口大骂将他拳打脚踢踹翻在地上,土匪气焰极其猖獗,却没有一名警察制止。可见对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的迫害政策警察们都心知肚明;这还是有目共睹的公开迫害,回到队里,更不知他们这些奉行“真、善、忍”的哥哥、叔叔甚至爷爷们又要被施以怎样的残忍折磨。有一次,警察在操场上体罚修炼者时,我看见所长张京生从操场边路过,他看到了施虐的场面,一句话不说便扭头走了。对于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根本不讲法律的:肆意剥夺正常睡眠甚至连续十多天不让合眼是常有的事,我在团河劳教所亲眼见到被这样迫害过的就有许多人;许多学员都曾因不放弃炼法轮功而惨遭高压电棍电击,为欺骗外界,封锁消息,警察一般都将学员拖到没有人的地方堵住嘴、捆到床板上秘密电击,而且每次都是好几根电棍同时电击。至于说法轮功修炼者的起诉,在当今被标榜为“法治”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劳教所这样的“执法单位”,更是得不到半点结果,表面的“幌子”都是做给外界看的。
2002年12月5日,团河劳教所管理科一名警察来集训队给我做笔录时,态度强硬地告诉我说:“不转化就别想离开‘两劳机关’(指劳教所和劳改所)!”
2002年11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党办主任冯世勇等到团河劳教所措辞强硬地以“彻底转化”作为我劳教期满后复学的条件。2003年春节左右,学校宣布将我除名。
2002年12月19日,迫于舆论的压力,团河劳教所将我暂时释放,但在此之前610办公室却通知了我的学校、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及我的家人到劳教所共同签了一份旨在不准我继续修炼的协议,对我实施严密监控。
2003年新年前后,我从家人那里得知学校已因我不放弃修炼将我除名,户口被打回原籍,至此,作为已没有单位作“担保”、又没有转化的法轮功修炼者,我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到当局办洗脑班等剥夺人身自由以至更严重的迫害。而610办公室对被送洗脑班后仍拒绝转化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一贯作法就是判处劳动教养。近期我又获悉:北京公安向当地公安传达命令,搜集我的材料,掌握我的行踪,并欲将我抓捕后判刑。因为我亲身经历和了解许多团河劳教所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内幕,又没有转化,所以就成为重点监控对象。
在2002年12月19日晚被释放前,610让我父亲签了一份株连家属的非法协议。释放当晚,劳教所管理科任科长和集训队的一名警察;学校保卫科、学生处领导;学校所在地警察三方将我和前来劳教所接我的父亲在严密控制下送进了返回原籍的火车。管理科长授意火车乘警一路监视我。学校所在地警察向我父亲询问并记录了原籍当地派出所情况及我家电话。回到家后,就有警察往家打电话问我的情况,父母十分恐惧、担心,因为目前很多地区还有很多一名不闻、一直在家,没上过北京上访的,只要还炼法轮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关押、毒打、罚款和洗脑,都是在晚上从床上被强行抓走的普通老百姓,因为政府追踪所有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只因他们坚持法轮功好。躲在家里修炼法轮功并不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
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监控镇压遍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中国大陆千千万万被迫害的情况看,只要你炼法轮功,江氏集团就要动用国家机器迫害、打压,不讲法律、惨无人道。象我这样的情况,已经成为重点迫害对象,且情况危急,虽然我目前已脱离劳教所这个中国的集中营,暂时保全了性命,但仍然随时面临着会被通缉、随时会被逮捕、从而再次遭到更严酷的迫害,也就是说,在江氏集团根本不讲人权、法律的无所顾忌的打压迫害下,我随时面临着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在此我紧急呼吁,请求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请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请求国际反酷刑组织、请求国际大赦组织、请求国际上一切关注人权、爱好和平的正义组织和一切正义人士对我进行紧急援救!同时也对正在象我这样正被残酷迫害、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紧急关注和援救!(完)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4/8/31/519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