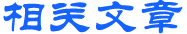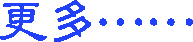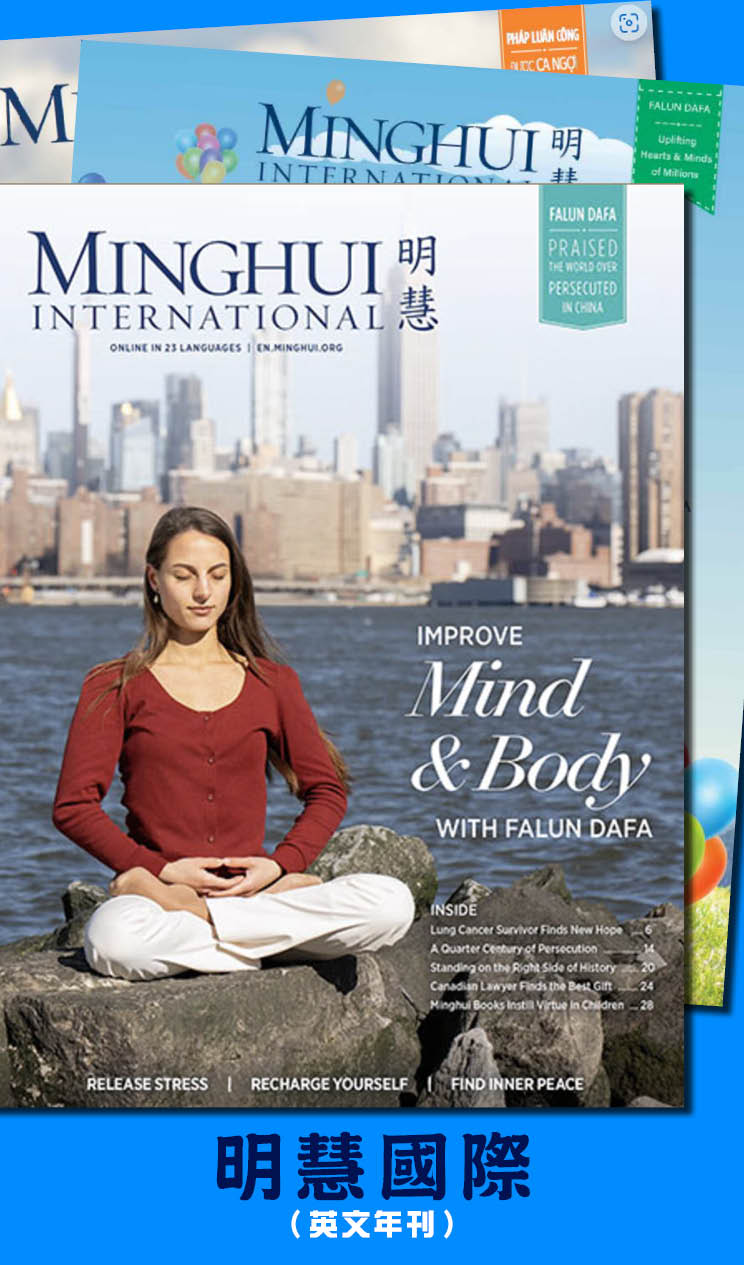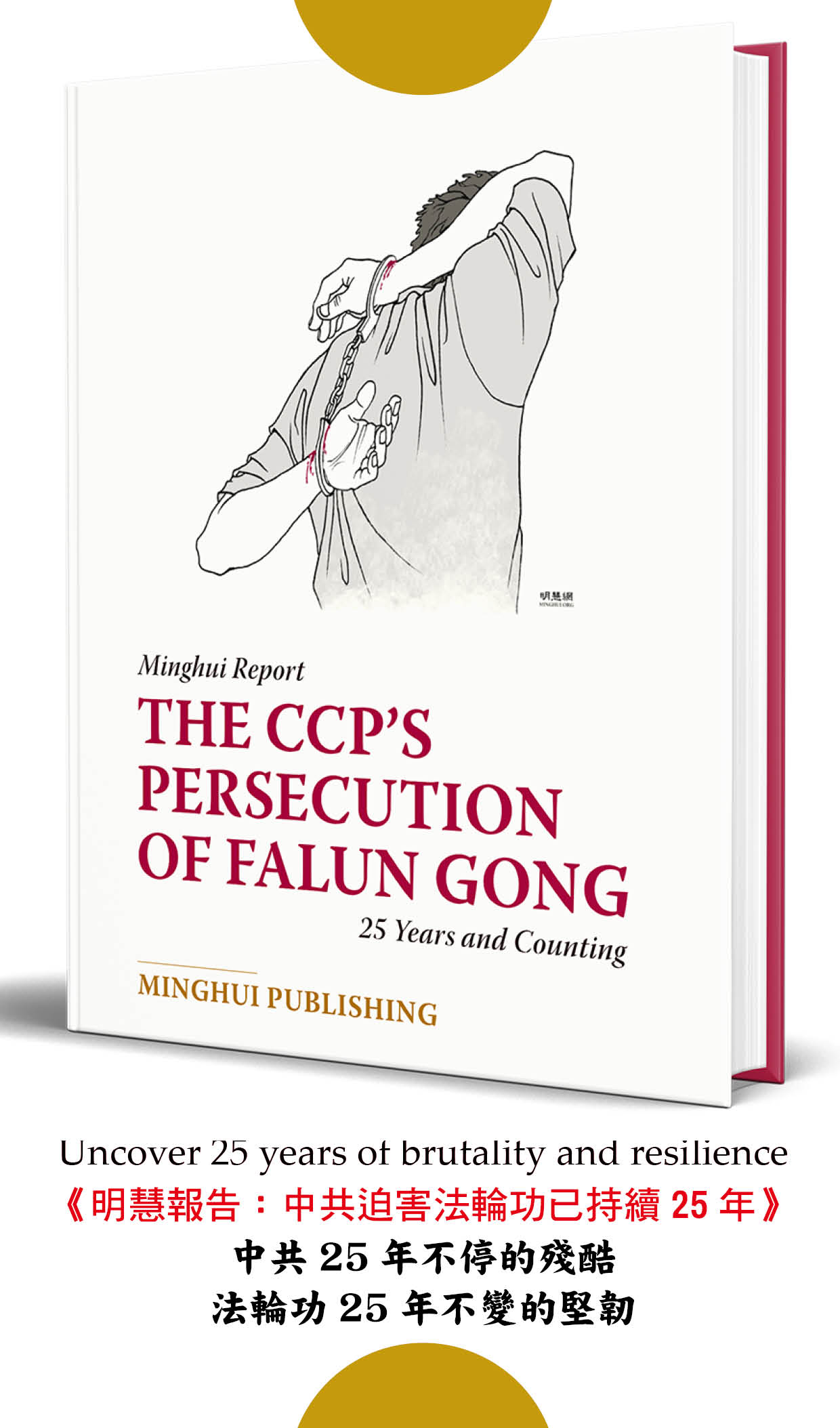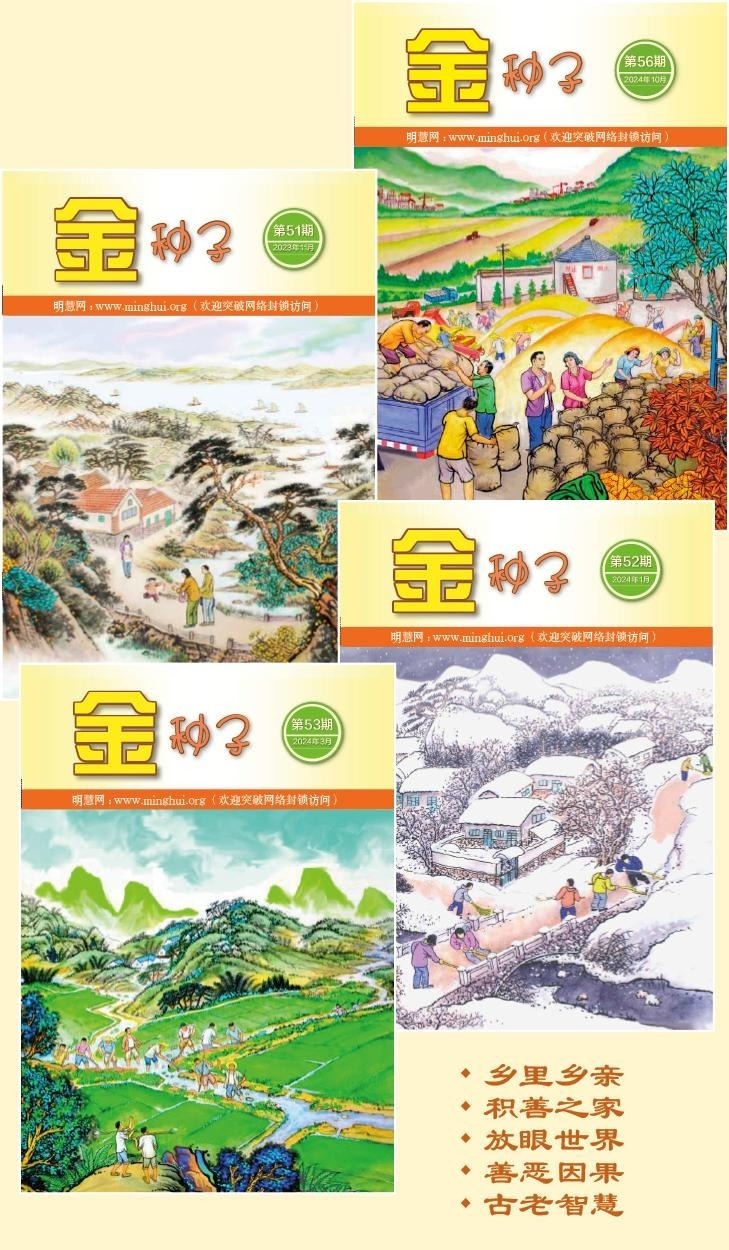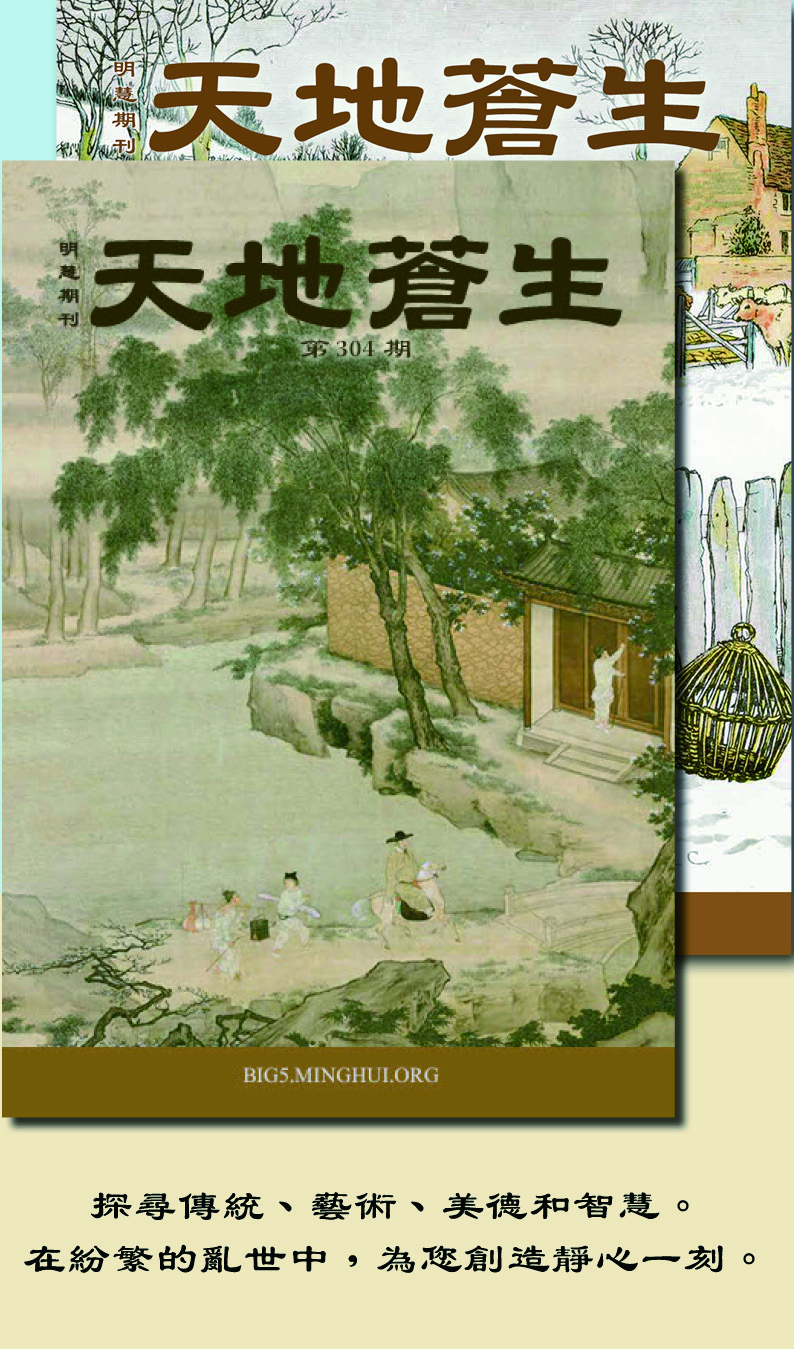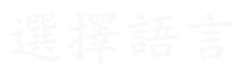农村女青年修炼初期的经历:去北京证实法
走入大法的欣喜
有一天,丽大姐来到我家说:“咱俩炼功去吧,你也腰疼,我也腰疼,人家说炼功就炼好了。”我说:“我哪有时间炼呀,孩子这么小,还得去地里干活。”大姐说:“一天你还抽不出一个小时的空呀。”丈夫说:“炼去吧,炼炼就不腰疼了。”大姐看我不想去,又说:“人家这功叫法轮功,我哥和我妈炼哩,这功炼着炼着有人就飘起来了,有个老太太,人家在床上炼着炼着,就飞到别处去了。”我知道她看我不想去,说点神奇事。我心里说:这功我也没听说过,那人还能飞起来,我才不信哩。我心里这么想,但是没好意思说出来。在大姐的劝说下,在丈夫的支持下,就这样,我得法了。
得法后的心情是无法言表了,那个激动啊!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好的法,叫我知道了这么多常人不知道的法理,也不愿意和常人在一起说闲话了,整天就是跟大姐同修在一起说修炼的事,一起学法,走起路来都是抬头挺胸。师父说:“我们给你这么多东西,叫你知道了这么多常人不该知道的理,我把这个大法传给你,还要给你许许多多的东西。”(《转法轮》)我觉的我有师父了,师父讲了这么多天机,常人知道什么呀。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欢喜心,现在看来,这心这么严重。
初遇“四·二五”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们这个村炼法轮功的就有几十个人了,年龄大的七、八十岁,年龄小的才几岁。都在一名同修家的大院子里学法、炼功,到各村去洪法。
记得一九九九年“四·二五”的前天晚上,大家齐心想去北京证实法。因为当时村里有车的人很少,我们十多个同修租了一辆面包车,在车上大家挤着到了县城。下了车,眼前人山人海的,都是同修。去北京的车很少,根本拉不了这么多人。最后决定一个村只去两个人,剩下的同修都返回了家,我也跟着回来了。
“七·二零”:去北京证实法
到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同修们都要走出去证实法,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一天中午,我们商量好准备去北京,村里没有去县城的车,镇上才有大巴车。我们村离镇上有十几里的路,当时都是土路,怎么去呢?我说开我家拖拉机去吧,到了镇上,再把拖拉机放到镇上的亲戚家。
到家,我跟丈夫说要开我家拖拉机去,他说:“还是我送你们去吧,我把拖拉机开回来,还得拉东西用哩。”就这样,他拉着我们满满的一车人去了镇上。没拉完,剩了几个老年同修。
刚到镇上,就开过来一辆大巴车,这车好象是专门来接我们的,一点没耽误功夫。售票员看着我们笑,说:“男女老少这么多人!”确实那天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七岁。她知道了我们是炼法轮功的,要去北京。司机说:“现在到处都在拦截炼法轮功的,我不能拉你们到汽车站,你们必须提前下车,要不就被抓走了,车站有很多警察和便衣。”
我们刚到县城,就下了车,知道车站是不能去了。甲同修认识路,他领着我们绕开车站,徒步前行。三三两两的还得分散着走,不然就会被盘问。
七月的天骄阳似火,可同修们没有一个说热、说累的。
我们这一群同修,都是平时很少出远门的、老实巴交的种地的农民,哪知道北京在哪呀。甲同修带领我们拉开距离前行。天渐渐黑了,刚到下一个县城。突然有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过路的。可能那人是便衣吧,不由分说就拉我们上了车,也不知道往哪拉。等下了车,看到是在一个大院里,应该是一所学校,这里被他们劫持来了好多同修。他们翻看我们的包,有同修带的大法书被翻走了。我的包里只有一个水瓶子和一包纸。然后,又按各个村镇分成一排一排的,接着叫来了很多辆大巴车。我们村的同修上了一辆车,连夜又把我们送回了村。
下车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们几个同修商量着:坐车是去不了北京了,那我们就骑自行车去吧,我们几个都是比较年轻的。我到家,孩子们还没起床,我跟丈夫说:坐车去不了,我们骑自行车去。我拿了三百块钱,到炼功点的同修家吃了他家一碗小米粥,我们就出发了。
这次是六个同修,其中两人是母女,女儿同修只有十三岁,也骑一辆“大二八”。我们一行六人拉开距离骑,还是由甲同修带队。可是没走多远,就有一名同修没跟上来,走散了。后来她说没看到我们往哪边拐弯,找不到我们,自己就往前骑,然后遇到了其他村的同修,同行也到了北京。我很依赖同修,因为没出过远门,又是骑自行车,不知道哪是哪。
我们五个人不敢走大路,因为到处都是便衣拦截、盘问。走一些小路、土路,渴了就从浇地的井口接点水喝,饿了就从道边小摊买点吃的。到了傍晚,下起了雨,我们从村里的小店买了几个雨衣,又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点面条。晚上,雨还没停,也不能老在饭馆坐着,还得往前走。
我们推着车子到了村外,在路边坐下,等雨停。我只觉的长这么大没这么冷过,因为是大暑天,我出门时只穿件连衣裙,披个雨衣。同修们都很冷,我们坐下,背靠在一起,我觉的只剩下心脏是热的,还在跳动。我知道是去我怕热的心,怕热只穿件纱布连衣裙。甲同修说,咱们去找个能避雨的地方。摸黑我们找到一所刚盖好的房子里,还没安装门窗。
天还没亮,雨停了,我们离开这里,继续往前走。雨是停了,可是土路太泥泞,走不了了,只好上大马路了,也不管他盘问不盘问,拦截不拦截了。雨过后是大晴天,太阳光很强烈,同修们都是穿的半袖,晒的皮肤很疼。没有时间停歇。到了下午,我和同修们骑着车都开始发困,只能从路边摊买根冰棍,边吃边骑,这样就不会摔倒。
那对母女同修和另一名同修和我们走散了,只剩下我和甲同修两个人了;我很依赖同修,因为没出过远门,并且是骑自行车。走着走着,路边几个人把甲同修拦住了,我没下自行车,从他们身边骑过去了,他们象没有看见我一样。我走了一段路,确定他们看不见我了,我就停下来,在路边等甲同修。等了好长时间,没等到同修,我想可能同修被拦截回去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单枪匹马闯北京,边走边问路。天渐渐黑了,我顺马路走着走着,前面靠边停了一辆货车,看到司机在修车。我问司机:去北京怎么走?司机吃惊的说:“你怎么上高速了,这是高速,太危险了,你赶快出高速,这里已经是北京的地界了。”司机帮我把自行车从栏杆搬了出去,我翻过栏杆,谢过司机,顺高速边上的小路前行。
不知走了多远,自行车前胎没气了。这里已经有了路灯和楼房,有了城市的气息,打听着哪里有修自行车的。推车前行的时候,我困极了,走着就困的直打晃。在街边,我找到了修理自行车的。修好以后,又困又饿,找了一个小饭馆,八块钱吃了一碗热汤面,饭店里的人都好奇的眼神看着我。吃完饭,不知道几点了,我想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不远处,就看到了一个乒乓球台——师父赐我一个球台睡觉。当时我想我要记住这个地方,晚上还来这个球台睡觉,可第二天晚上,就再也没找到这个球台。
白天买两个馒头,用矿泉水瓶接点自来水喝。我想,能找到个同修就好了,看到街边的人都不象同修。当时我心里觉的这次和“四·二五”一样,会有好多同修来北京,一起向政府反映情况,转了两天,没能见到同修。
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当时只有甲同修家有个座机,我就到一个小卖店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回去。接电话的是甲同修的妻子(同修),她告诉我说现在家里的很多同修被关在镇上,甲同修也被带走了,去北京的同修大多都回来了,这次没能证实了法,不知道怎么做了。我想,那我也回去吧。刚到家,就被带到镇上关起来了。回来时,裙子是土灰色的,胳膊和腿上晒掉了一层皮。
结语
那时,就我这个没出过远门的普通农村女子,在大法修炼初期,被大法唤醒了生命中的真念,在大法遭受迫害时,走出家门,只身单骑闯北京,真心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但也由于那时对法认识的不足,并没有达到初衷的目地。如今修了快三十年了,离不开师父的保护,还有同修的帮助,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跟师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