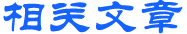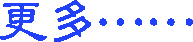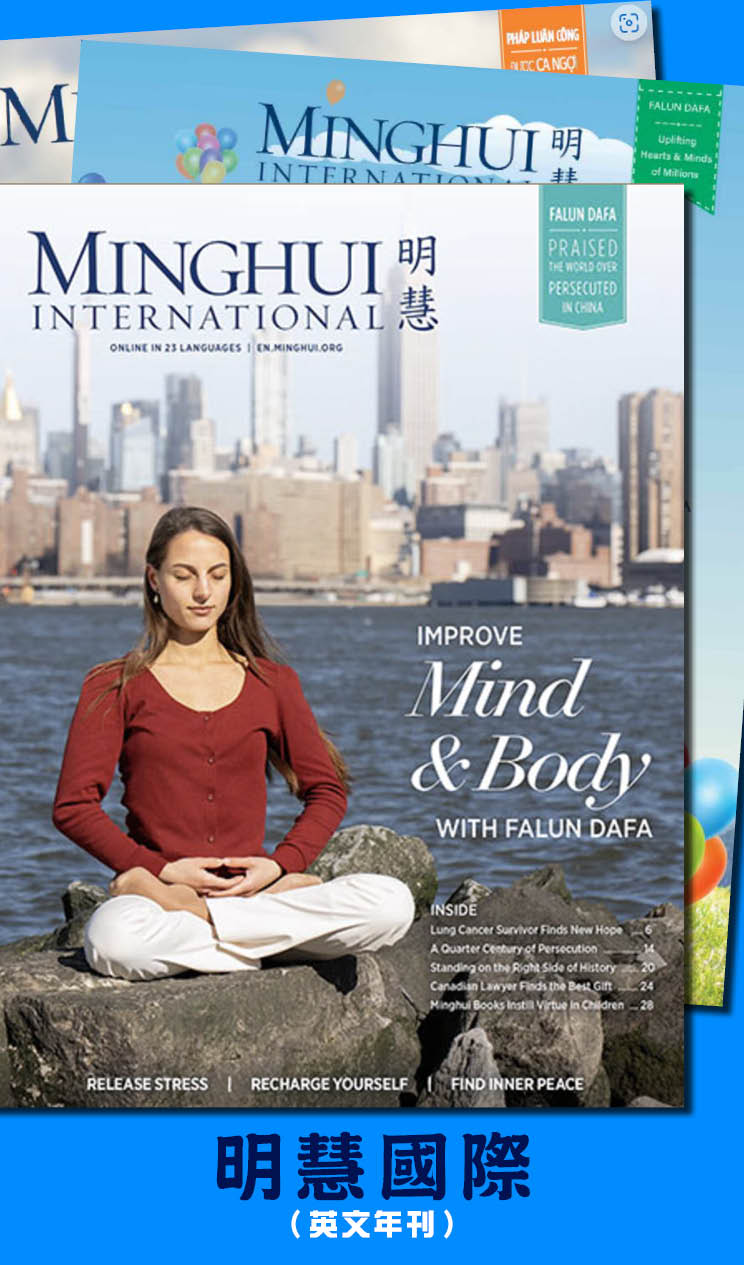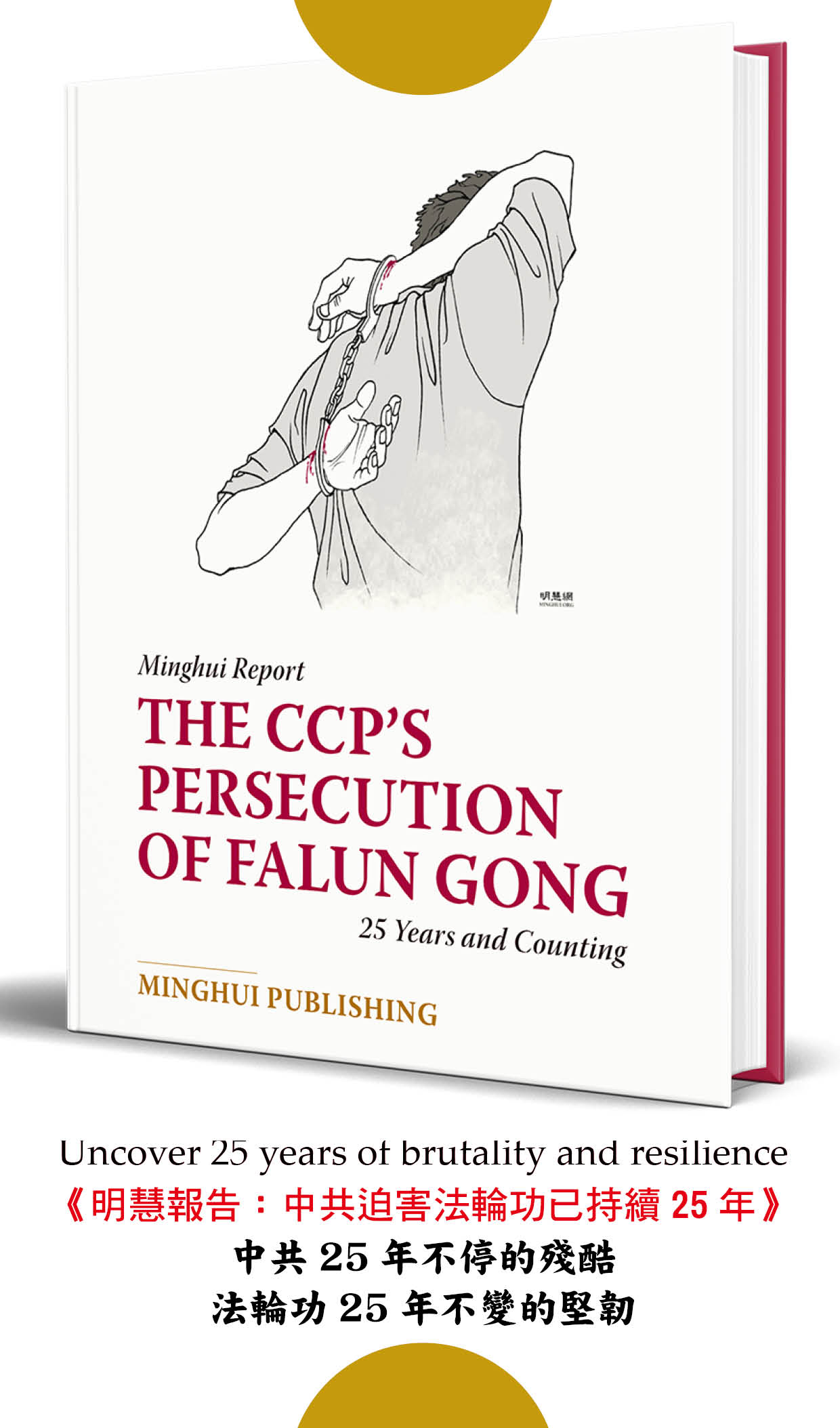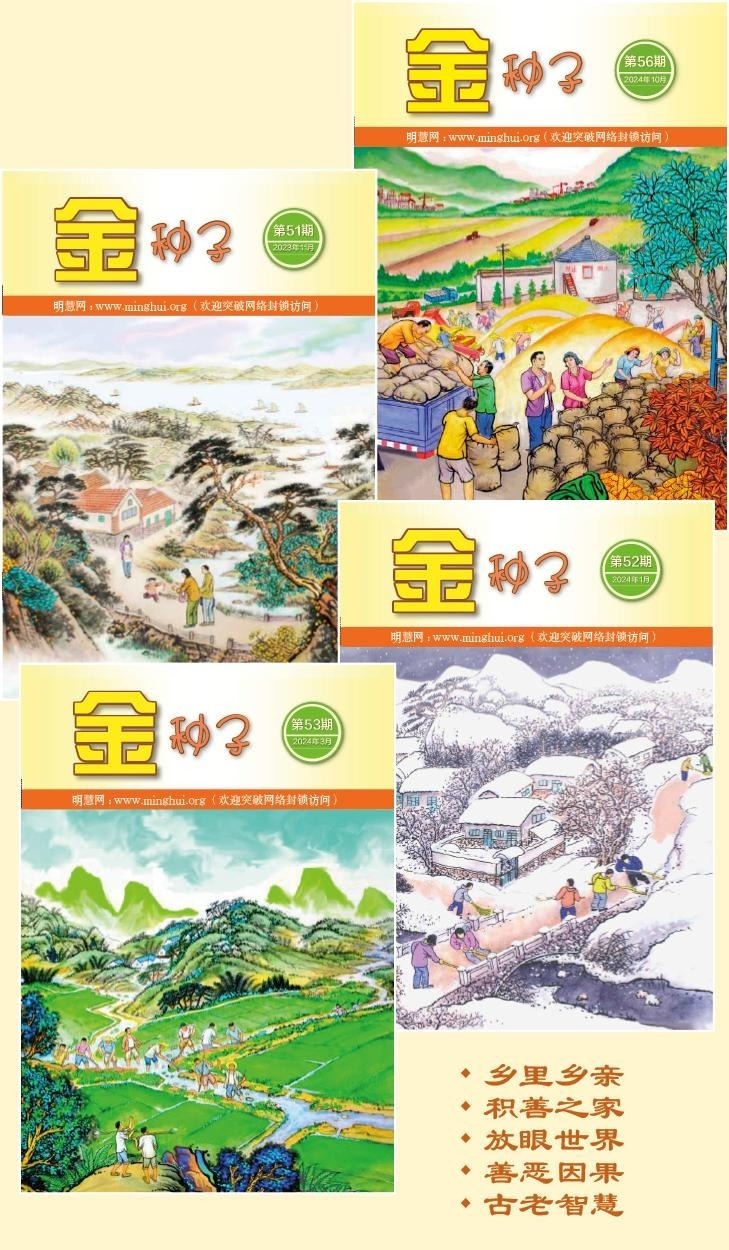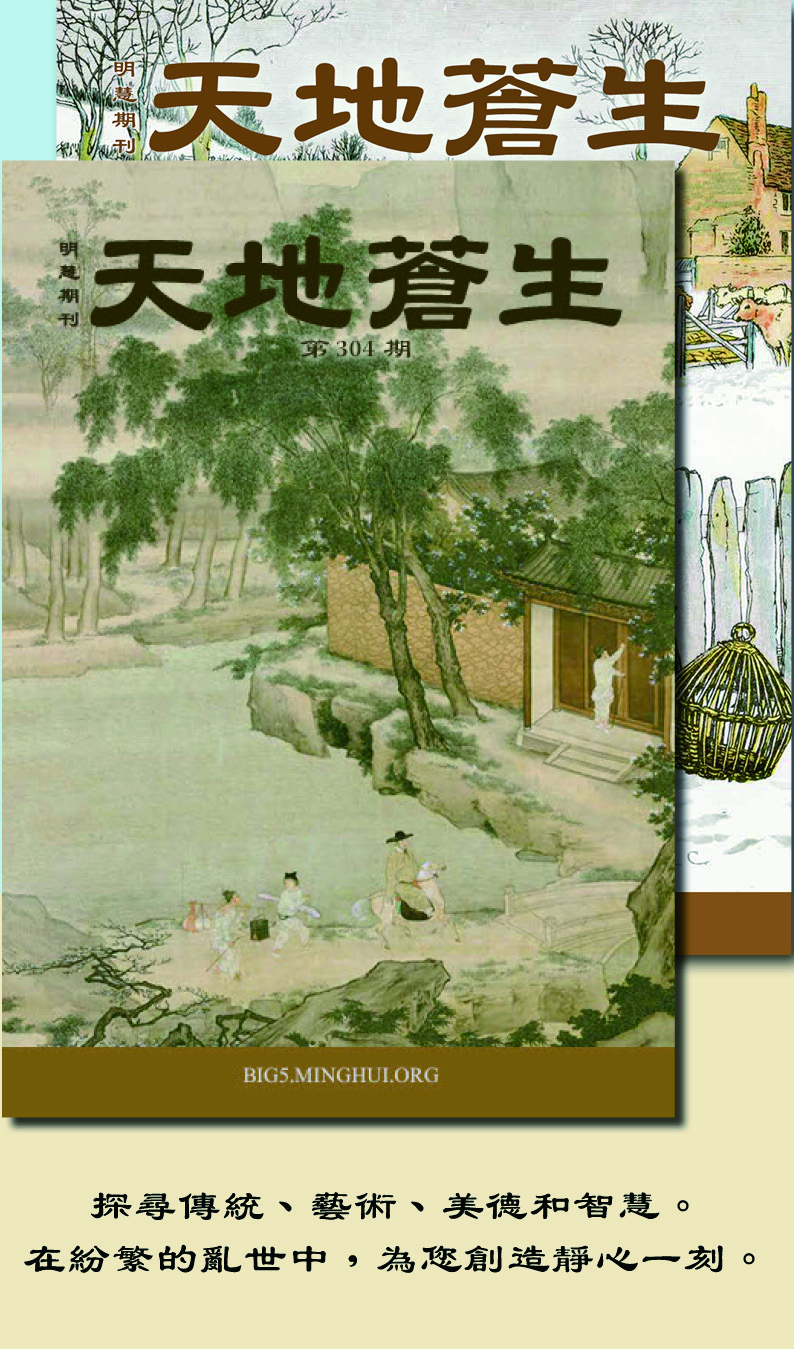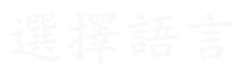我与大姐的修炼故事
一、大姐得法天目开
我大姐大我三岁,住在南方儿子家。她有多年的眩晕症,每年都要住院一、两次,已经七、八年了。她犯病时,突然倒地、呕吐、生活不能自理。我打电话告诉她:“你赶快回北方来,我炼法轮功后,失眠、胃病、气管炎、心律不齐,所有的病全好了,你的眩晕症一定会炼好的。”她问:“炼法轮功有什么要求吗?”我说:“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打麻将。不治病,师父给清理身体,按真、善、忍修心性,然后就无病一身轻了。”她说:“叫人行善啊,那我信。”
大姐回到东北后,我便去了她家。那时刚好有了师父在长春讲法的录像,傍晚我们去大姐家附近的同修家看录像,同修家墙上挂着师父的大法像,去的人很多,屋里挤的满满的,但放录像时,却鸦雀无声。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的教大姐炼功。我与大姐面对面站着,告诉她两眼微闭。这时,大姐说:“哎呀!我看见昨晚那家墙上挂着的那个人(注:师父法身)了,他在看我笑呢,就像‘八一电影’开演那样放光。”我很惊讶,怎么大姐刚要炼功就开了天目?太神奇了。
当天,一至四套功法,大姐都学会了。晚上,大姐和我去炼功点学法,炼静功。大姐根基好,当时就可以双盘,她在天目中看到自己在另外空间穿着黄色软缎衣服,半尺长的掐袖,戴着皇冠。她说,在天上,她是男的,有一张大大的案桌,而且非常威武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四点,我们去炼功点上炼功。炼完功回家路上,大姐告诉我,她看见师父坐在高山上,看见师父的侧面,她便问:“师父啊,我昨天看到的您是正面,今天怎么是侧面呢?”师父说:“早上晨炼的弟子很多,我不能单独面向你,你站的那个位置看到我哪就是哪。”然后,师父拿出一捆骨头,告诉大姐这是她的骨头,骨头上一块块黑了。师父就象弹衣服一样,轻轻的一拂,那捆骨头“唰”一下全部变成了白色,有的象透明玻璃一样。大姐心想:我看看前面领(炼)功那个小伙的骨头,一看他的骨头很黑。大姐问师父:“前面领(炼)功的小伙人挺好的,他的骨头怎么那么黑呢?”师父说:“不是今生今世造的业,”并且说大姐是个顽皮的小学生,又嘱咐大姐要好好修炼,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等等。
当天我跟大姐去书店,请回了一套大法书。我哥和嫂子与大姐家离的很近,后来他们也走进了大法修炼。三个妹妹也看过《转法轮》书,可能是机缘不到,没能走入修炼。
那天买书回来,在我要回家之前,对大姐夫说:“法轮功祛病健身很神奇,而且不要钱,你也炼吧。”姐夫说:“我不信,不要钱,你们师父吃什么?”我当时很生气,说:“不炼拉倒,没人强迫你。”
我和大姐家不在一个城市住,坐火车要好几个小时。我回家后,有一天,大姐打电话说大姐夫每天早上都去炼功点观看,看了几天,也开始炼上了,而且他天目也开了,能看到长胡子的道人在竹林里喝茶、下棋。我和大姐经常通电话,大姐说,炼功后没再犯过眩晕病,偶尔觉的有点晕,走路脚象踩在棉花垛上,可是不会晕倒,不影响学法炼功,一两天就好了。
二、我是来修炼的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开始了疯狂的打压,大姐和姐夫、哥、嫂都胆小,开始时,躲在家里偷着炼,失去了集体炼功的环境。虽然都知道大法好,可是觉的政府不让炼了,无可奈何,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渐渐的放弃了修炼。
我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劳教。回来后,我去大姐家,得知姐夫已病逝,大姐因受邪党电视的洗脑宣传,误认为姐夫没及时去医院治疗导致死亡,所以她也不炼了。
我很难过,大姐的根基那么好,不炼太可惜了,我耐心的和大姐沟通交流。我带去师父新经文《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念给她听,大姐慢慢明白过来了。她又和我一起炼功了,抱轮时,大姐说她看到师父了,师父告诉她说:“能跟上,能跟上。”
后来大姐去了南方儿子家。她在那里接触不到同修,我比较担心,经常打电话嘱咐她千万不要放弃修炼,有新经文,我会想办法寄给她。后来,我被非法判了重刑。出狱后,我打电话问大姐情况,她说有时炼有时不炼,就是带修不修的。
二零一五年时,许多大法弟子向两高发出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状诉讼。我也向两高投了诉讼状,并收到了回执。我建议大姐也参与诉江,大姐说她也没被判过刑,不想诉。我说,你虽然没被抓过,可是你妹妹被关监狱,你一定很难过,再说你失去了集体炼功环境后,放弃修炼好几年,原来的疾病又犯了,打针吃药,花钱又遭罪。这些都是江泽民迫害给造成的,你要控告他才对。大姐同意了,并发出了诉江状,收到两高回执后,大姐在天目中看到,她穿着古代服装,站在一只小船上,从芦苇荡中划出来,出来不远,就飞上天了。
二零一七年,大姐说她腰扭伤了,卧床起不来了。我说,一定是因你修炼不精進了。她说:是。大姐在南方儿子家,接触不到同修,带修不修的,无聊时在电脑上打麻将。腰扭伤后,她在天目中看到两个人把她按在凳子上,拿大板子打她屁股,打的可狠了。她决心以后再不玩麻将了,好好修炼。腰渐渐的好了。
二零一八年,大姐回到东北。姐妹们聚到一块,妹妹和妹夫们都爱打麻将,大姐好了伤疤忘了疼,又跟着玩上麻将了,腰再一次受伤,这回卧床不起。
我知道后去她家。大姐家是老楼,她儿子想给她换个座便,可是拆完后,新买的座便器是弯口,安不上,他就用砖临时垫着用,说对付到春天再说。可是,临时座便就摆在砖上,满屋子都是下水道返出的臭气。外甥靠打工为生,没有太多时间。看我来照顾大姐,他就回自己家了。
大姐看到我之后,躺在床上嚎啕大哭,后悔、绝望。看到那场景,我也难免心酸落泪。我劝大姐想开些,咱们有师父管,师父说过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咱们学法、炼功,很快你就能站起来。大姐说,她女儿给她去医院拍了片子,说她有一节腰椎裂缝了,还有一节因骨质疏松剩三分之一了,医生叫贴膏药慢慢养。
我跟大姐说,有一位同修叫马忠波,双侧股骨头坏死,多年瘫痪在床,炼法轮功后神奇的好了,医生都感到震惊。
大姐说自己起不来咋办?我说,先躺着炼。我们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再学各地讲法。我联系上两位当地的同修,帮大姐发正念,清理大姐空间场的干扰。发正念时,大姐在天目中看到男女老少很多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四下逃跑。我告诉大姐,我要住到她能自己站起来,再回家。大姐的心情渐渐的好起来了。
我雇人把旧卫生间拆了,安装座便。搞过装修的人知道,装修是个非常费心费力的活,要找人、买材料等等,东跑西颠。我虽然七十多岁了,可是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干多少活也不感觉累。大姐拉屎尿都在床上,我帮大姐擦洗身体,处理大小便,把大姐的床单、被罩及她穿的衣服洗的干干净净,每天做可口的饭菜。一边照顾大姐,一边张罗装修大姐家的卫生间。
我让同修帮我联系安装接收新唐人的大锅,来了一位男同修,他说没见过我。我说,我是外地来的,我大姐也炼法轮功,可是她不精進,带修不修的,现在腰伤了起不来,我来照顾她。男同修说:“你不是来帮你姐,你是来修炼的。”我觉的他说的话很在理,他的话对我提高心性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改造大姐家卫生间,我跟大姐商量,墙全部用铝合金玻璃,占地面积小又美观,而且价钱和水泥砖砌的一样。可是,大姐就不同意,她说她喜欢砖砌的。我想自己是来修炼的,不和大姐争辩了,就按她说的办吧。我去找瓦工,谈好了价钱,过两天来干活。
这时,大姐的儿子回来了。大姐跟她儿子说:“你二姨让做铝合金的,我不同意,我喜欢砌砖的。”外甥说:“还是二姨说的方案好看,你躺那瞎管啥?”没想到,大姐又改变了主意,说:“那就做铝合金的吧。”第二天,我把瓦工辞掉,又去找玻璃店。如果不是男同修提醒我,我肯定会对大姐的做法产生怨气。当我想到自己是来修炼的,心里就很坦然了,一点怨气都没有。而且,想到能多接触人,还可以多讲真相救人。我能接触到的人,都给讲真相、做三退,有同意退的,也有不同意退的,多数同意。
玻璃店老板来家安装时,我问他:“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了吗?”他很严肃地说:“法轮功?你有没有退休工资?”我说“有啊。”他说:“你拿着共产党的钱,还反对共产党。”我说:“我的工资是自己多年工作挣的,再说习某某也是老百姓养活他呀。”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爱听。”我说:“你不爱听,那我就不说了。”
他一个人来安装,我在旁边帮他扶玻璃,他不小心把一块两米多长的大玻璃碰掉一小块角,他长叹一口气,很无奈的样子。我知道那么大一张玻璃要装车拉回店,再重新割一块,拉我家来,很麻烦,很辛苦。我从地上捡起那块小玻璃碴,找到透明胶说:“这块玻璃是固定不动的,也不显眼,粘上就行了。”他紧锁的眉头一下展开了,立刻照我说的把玻璃安装上了。
然后,他说:“大姨,我有个铁哥们,是专抓法轮功的,经常到我店里蹲坑,从我店的窗户,看到对面街上有老太太贴不干胶或者发资料的,他们就出去抓。”我说,他虽然没去抓人,但是他等于帮他们抓了,对他很不好。既然是铁哥们,你要劝他别再干这种傻事了,这个罪是很大的。他说,这两年不太抓了。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我觉的他背后的邪恶被我的善念解体了。所以,他才主动和我聊起法轮功的事。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了善的力量。
四十天后,大姐能下地了,看到新装修的卫生间,乐的嘴都闭不上了,大姐说非常感谢我。我说,不要谢我,要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快过年时,我回家了。
二零一九年末,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大姐的人心重,同修去找她,她怕传染,不让同修进屋。一个人修炼很容易懈怠,她又带修不修的了,又一次卧床不起。她告诉我,因抬洗衣机,把腰扭伤了。我说,那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你修炼不精進了。大姐说,是。
她家儿女都工作,妹妹们都有丈夫和家,虽然常去看望大姐,但不能住在大姐家时常照顾她。我又一次去了大姐家。大姐后悔莫及。她躺着把《转法轮》翻到师父法像那页,双手合十,痛哭流涕,求师父原谅她。看她痛苦极了的样子,我不敢再责怪她,只能安慰她。
我们每天多学法炼功,当然我们之间也会有矛盾发生,那时新唐人电视正播放一个时事新闻,大姐的党文化挺重,她很反感电视节目中的说辞,我和大姐争辩起来,她说:“你不是中国人吗?”我也用很尖刻挖苦的语言和大姐争辩。事后,我向内找到自己也存在党文化的流毒,强加于人,我向大姐道歉。我俩一块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听完后,大姐的党文化流毒也去掉许多。将近两个月时间,大姐能下地了,她又一次站起来了。
三、在我家也是修炼
二零一九年,我妹妹和外甥们商量说要把大姐送养老院去。我不同意,在养老院,就无法学法炼功。我跟外甥商量,叫大姐到我家住。我也是一个人住,我说我们俩还是个伴。外甥就把大姐送我家来了。
大姐来我家后,每月要给我一千元生活费,我坚持不要,因我经济条件比她好。我女儿让我象征性的少收一点,说这样大姨住的安心一点。我说,那就收五百吧。大姐不同意,说去养老院每月要一千五百多,而且吃住条件还没你家好。大姐原本就是一个善良宽厚的人,修炼后,更是守德贤惠,我不想和她争辩,顺其自然,每月收她一千。
我俩在生活上从没发生过矛盾。可是在修炼中却矛盾不断,我想让大姐尽快的跟上,她到现在还不会背《论语》,就和她商量说:“大姐,你背《论语》吧。”谁知大姐硬邦邦的回一句:“不背。”我问:“为什么?”她说:“我脑子不好使。”我一下子火了,大声嚷:“你脑子不好使,唱常人歌,你咋能记住呢?”大姐说:“你让我站,我就得站,你让我坐,我就得坐吗?”我说:“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懂好赖了?叫你背《论语》,是为你好。”大姐说:“你这种态度为我好,我也接受不了。”大姐生气了,两天不说话。
过了几天,大姐说:“我心里闷的慌,咱俩心平气和的唠唠。”我坐大姐床边,说:“行。”大姐说:“你不能象对老三、老四那样对我吗?那天,你对我的态度我实在受不了。”说完,便委屈的大哭起来。我想,是呀,我怎么就没站在大姐的角度去为她想呢?我对她发脾气,会让她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师父最近几年的新讲法多次讲到让我们修好自己。可自己修的这么差劲,自认为对别人好,就强加于人,说话尖刻不善,魔性很大,根本不是修炼人所为。我很愧疚,说:“大姐,我错了,以后再不对你发脾气了。”大姐说:“我心里也知道你为我好,可是就是接受不了。”我说;“我要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我改。”
过了两天,大姐告诉我说,她背会《论语》了。我俩每天一块学法炼功,大姐的腰恢复的也很快。自从大姐会背《论语》后,感觉她修炼的状态好多了。有一天,我们学到第四讲(每人念两页),该我念时,大姐用手示意,她要继续念,念完后,大姐说,刚才她念法时,感觉自己不知是她进到书里了,还是书进到她身体里了,非常奇妙的感觉。
其实,我很想听大姐讲她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可我知道那是一种执着心,我克制自己,从来不问大姐,避免给大姐修炼造成损失。大姐这么多年在天目问题上一直把握的很好,带修不修时也能看到,没有那个显示心。她说,每天都能看到,睁着眼也能看到,但她很少说,偶尔跟我说说。
有一次晨炼时,大姐说,她看到我站在天上,背后是高大的殿堂,半截身在云彩中炼功呢。还有一次,抱轮时,她天目里看到一个大字,象人一样大,让我猜是啥字。我说猜不到。她说是“情”字。我说:“师父在点化你的情还很大。”大姐说:“是啊,怎么去呢?”我说:“多学法,在法上悟。”
我对大姐有些事也是看不惯,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大姐对孙女牵挂,打电话嘱咐这、嘱咐那;妹妹们不打电话,她唠叨别人不关心她了;美国大选总统时,我俩也发生过争辩,我看了师父《大选》经文后,和大姐交流。她说,爱谁当总统谁当,跟她没关系,说她也不是美国人。我说,人得分清正邪与善恶。大姐说我老让她站队,她不想站。一到邪党“敏感日”,她就告诉我先别干这、别干那、避避风头等等。
我跟其他同修交流,我和大姐之间老有矛盾。同修说:“首先修好自己,扩大容量,不能用你的标准要求别人。”开始时,我老说大姐常人心太重,我经常说她,她很反感。经过与同修交流、学法,我向内找自己,站在她的角度理解她,很少说她了。明慧上有好的文章,我就念给她听,不说那种尖刻挖苦人的话了。大姐说我改变了很多。
大姐到我家住,对我提高心性,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我去大姐家是修炼,大姐来我家,依然是我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我要把握好这修炼提高的好机缘,和大姐共同精進,直到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