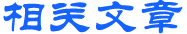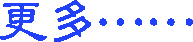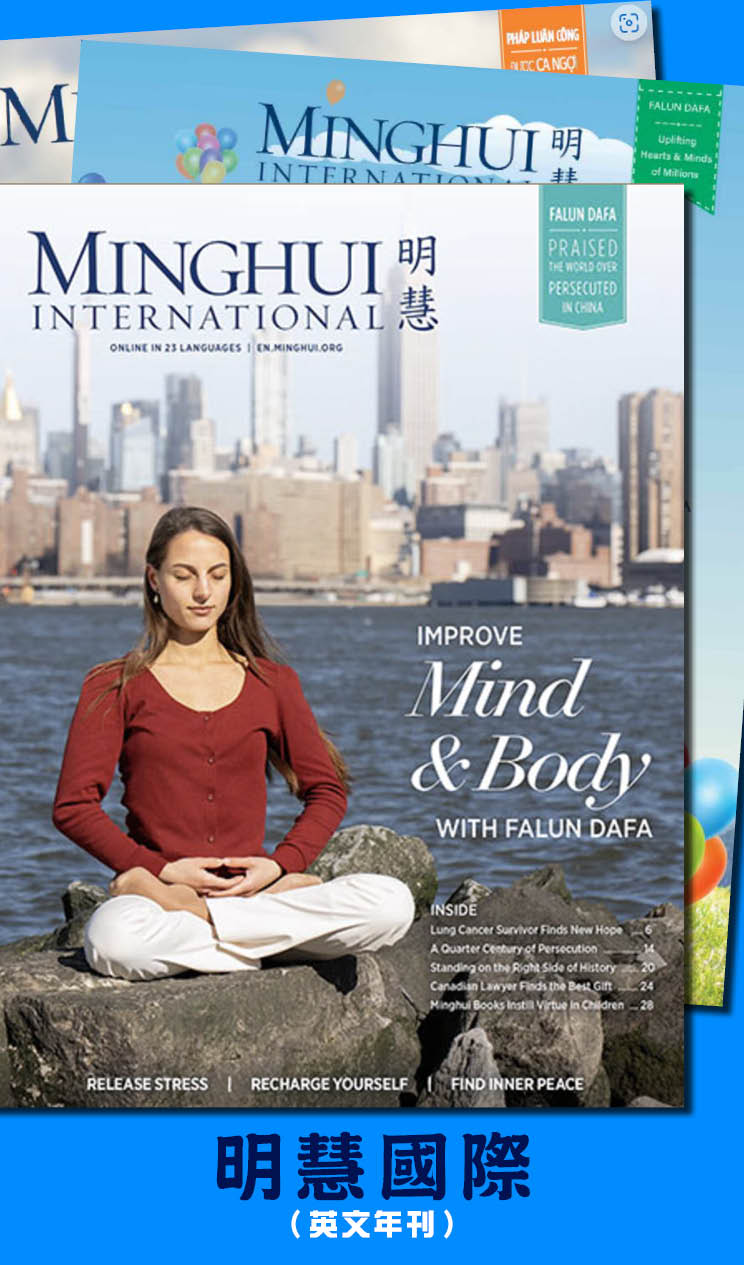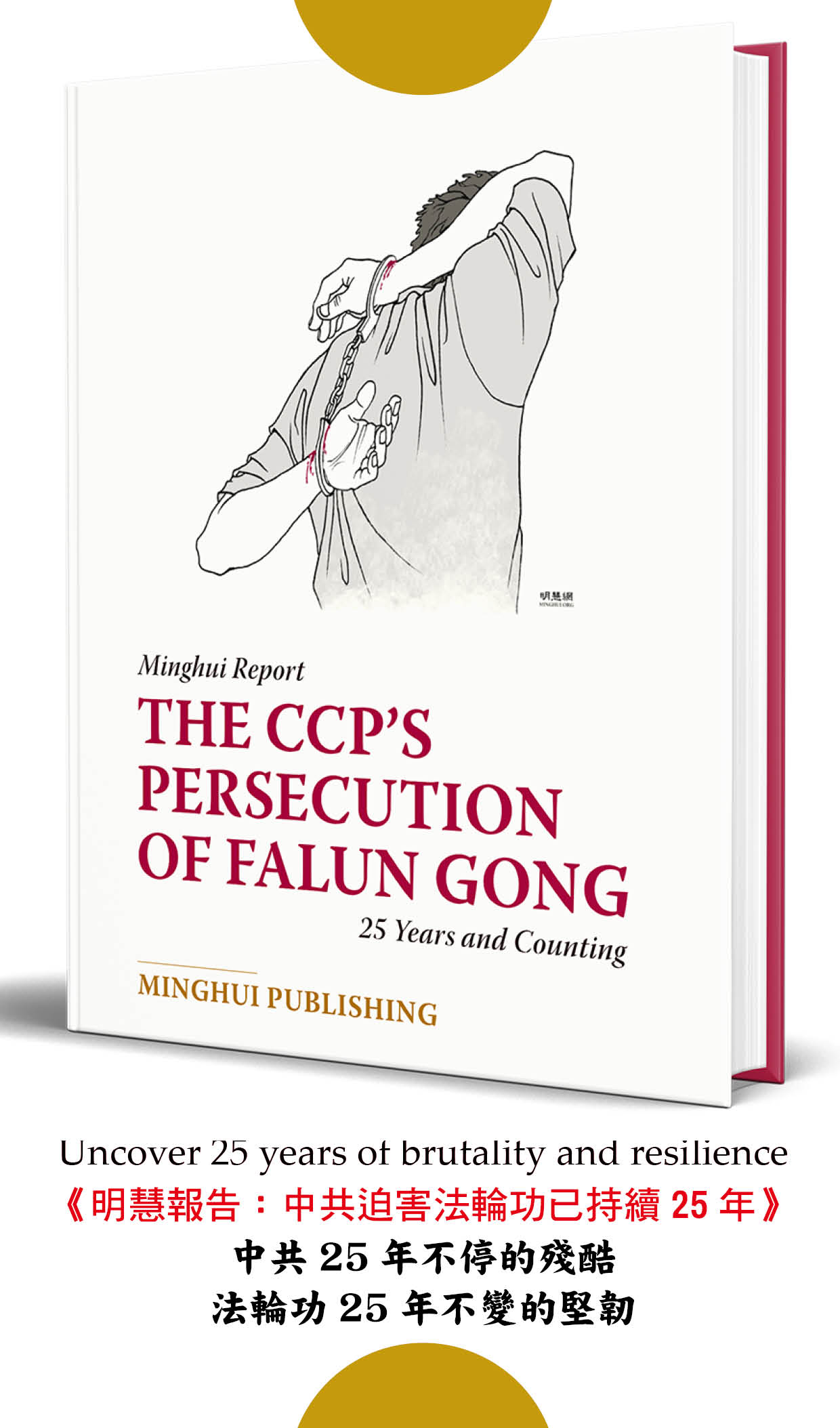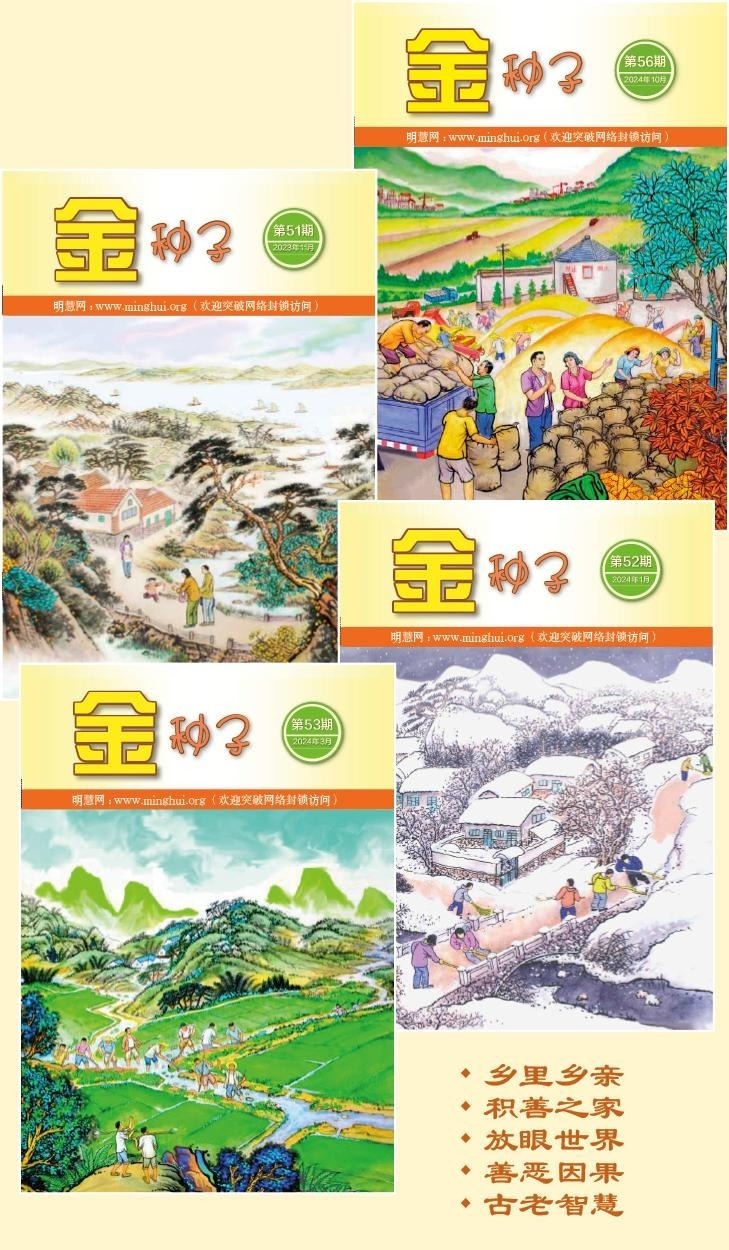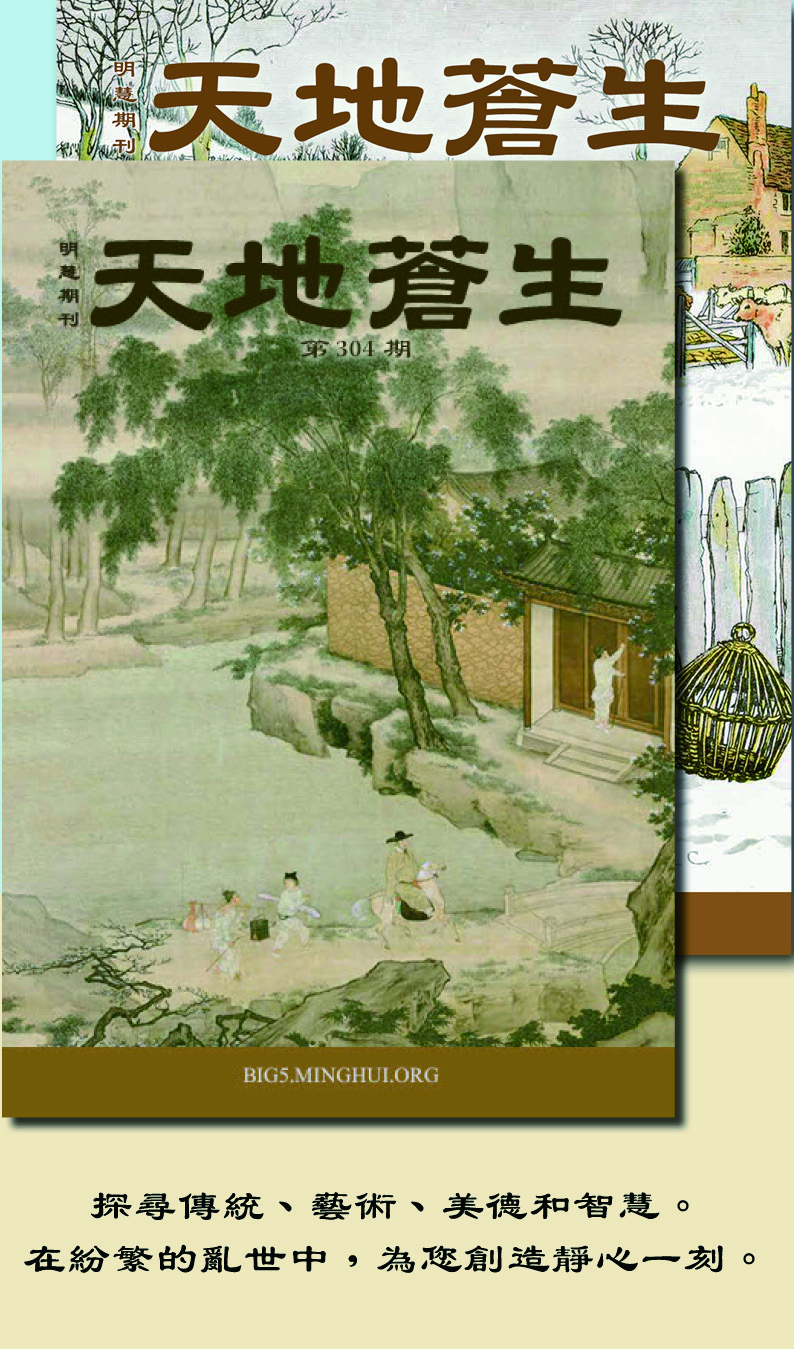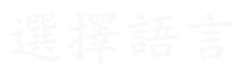在那风雨飘曳的日子里
——回忆“七·二零”后在北京走过的那段岁月
一、母亲独闯北京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经历过的每个同修想必都感受到当时的压力,一瞬间全国所有的媒体、电视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诽谤大法,我们都失去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七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具体记不清了),在甲地的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要去北京护法,匆匆几句就挂了电话,第二天就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母亲不见了,身份证也没带,换洗衣服也没带,钱也没带,可能去北京了。听到电话,我当时的心里很是牵挂,因为母亲当年六十多岁了,也没什么文化,平时出门都是有家人陪同的,现在母亲一人独闯北京,我的心是又佩服又牵挂。
后来的日子里,家里就不安宁了,父亲整日流泪,感叹平时对母亲的照顾不够,说母亲平时吃了很多苦,现在什么音信也没有,我那段日子心里也很难过,我们几个儿女都时时保持电话畅通,生怕错过一个电话、生怕母亲来电话未接到,期间只接到母亲一个电话,说在北京一同修家。后来,我与家人(未修炼法轮功)商量去北京找母亲,到了北京,一看到处都是便衣,警车,真可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你稍微在哪儿一坐,马上身边就有人过来了,在你身边观察你,我与家人当作旅游的样子,我们根据当时电话上的来电显示先去找母亲当时逗留过的北京同修家,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找到,满怀的希望化为泡影。那位同修说,当时她的家人在那种恐惧下,不敢让她收留大法弟子,所以母亲仅在她家住了一个晚上,稍微洗漱了一下又去天安门了。我与家人对那位同修表示了感谢,眼含泪水又踏上了寻母之路。我们没有目标的到处问、到处找,经常看到有大法弟子被抓的场景,同去的家人有点害怕,晚上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流了一夜的泪,与我说:“若妈妈现在突然出现了多好呀!我一定给妈妈买好多吃的,妈妈一定饿了……”找了两天没找到,我们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返回了家。
后来的一天,我去以前的一个同修处看看,在他那我遇到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从他与同修的谈话中,我听出也是大法弟子,我便与他们诉说了母亲的失踪,那位年轻同修告诉我:“不用担心,母亲应该是很好的,北京周边有许多大法弟子。”啊,我一颗心终于放下了,我回家将此消息告诉了家人,让他们不要太担心。
九月初,接到我们当地驻北京办事处的电话,与我们核实信息,然后说母亲在办事处,因母亲上访被截回,让家人去领。经全家人商量,决定由我与其中一位家人一同去北京接母亲。
到了驻京办事处,见到母亲的一刹那,觉得母亲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多,虽然晒黑了点,但精神状态很好。第二天,我们要带着母亲离开北京了,母亲说还想去天安门看一下,我们答应了母亲的要求,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母亲带着我们来到她曾经多次逗留的地方,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大法弟子,虽然大家都没说话,只是点一下头,但直觉告诉我都是同修,那一刻我觉得那个场是那么的祥和,我被吸引住了,我也好想留下来,可是最终还是带着母亲回到了我的居住地乙市。
二、母亲在北京的日子
回来后,母亲便给我们讲述她是怎样在师父的保护下辗转去北京的,及在北京四十多个日日夜夜。
母亲离开甲地那天是凌晨二点多钟在家人都熟睡的情况下,带着平时积攒的几百元钱踏上了進京护法之路。母亲说,出门在路上拦一出租车,花了六百元钱拉到某一地,这时天已有点微亮,又找一三轮车拉到长途客运站,母亲只知道当时甲地各个关卡查法轮功学员進京很严,没想到了这个小地方也一样,到处是警察,每辆车警察都上车一个人一个人的查验盘问,但母亲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的过了这一关。母亲没有直接到北京,而是在河北周边就下了车(具体是什么地方,母亲根本不知道下车的地名,只知道反正不是北京),又通过打听坐客车转地铁,跟着多的人流走,下了地铁出了站口,抬头一看天安门就在眼前,母亲那个激动呀,一个老太太一路就这样来到了北京天安门。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北京特别热,持续高温,刚到北京那天,母亲有点类似中暑的症状,又渴又饿又晕还伴随着恶心,母亲难受了就找个空地躺一下,渴了母亲就用个矿泉水瓶在洗手间或广场浇花水管接点水喝,还经常遭到管理人员的谩骂和不许,母亲刚去北京的时候跟着在北京结识的同修白天在天安门广场转转,晚上就露宿在广场周围的灌木丛中,没有垫的也没有盖的,经常被蚊子叮咬的无法入睡,再后来就与结识的同修到周边去寻找其他同修,炎热的酷暑加上身上所带的钱所剩不多,母亲说每天早上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有个大栅栏,那个地方的粥便宜,咸菜免费提供,每天早餐在那儿吃,也是一天最饱的一顿,吃完早餐再买两个馒头带着就是一天的饭了。
母亲说若没有师父的保护,怎样走过来想都不敢想。后来遇到一位天津的年轻同修,专门出来找外地同修,找到后带到北京一同修家,在同修家洗洗澡,修整一下,但由于同修家房子较小,加之外地同修流动量较大,所以每个同修一般暂住一晚就离开了,但不论条件怎样艰苦,母亲从未想到回家。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条件艰苦仅是一个方面,到处都是便衣及特务,经常诱骗着同修到某一地方集中,然后实施绑架,母亲就是由于听信了他人的传言说联合国来人了,母亲一心想向上面反映情况,所以母亲就与几个同修一同去了某地,结果被绑架。
三、我与母亲在北京的所见
在我家居住的这段时间听了母亲在京的经历,了解到当时北京全国大法弟子护法的情况,我也决定去北京,于是在护送母亲返回甲地的时候,我与母亲一同又去了北京。母亲凭着她在北京的记忆,带着我找到了她以前呆过的一个地方,幸运的是那个地方还有同修,当时在一个约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着七、八个同修,九月份的北京已有些凉意了,但同修们只是简单的地上铺着一个凉席,晚上就搭着自己的衣服睡觉。
当时有几个年轻的同修(好象北方同修)主要担任协调工作,他们先在周边将房子租借好,然后每天出去找全国各地来北京但没有住所的同修,将他们安置在各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来的同修多了,就将我们换到其它地方。后来将我和母亲安排在北京周边河北某一农村,是个院子,记得在这间农房里住了近二十人,为了安全,一般我们是不外出的,每天由一个同修外出买馒头回来,一天最多只能吃两餐凉馒头,没有菜,后来就有点拌黄瓜了,为了不引起周围村民的注意,所以馒头也不能买太多,那么我们每个人每餐尽量少吃点(没人约束,自己把握),为了减少声音,所以自来水尽量少用,实在是要洗了,我们就用毛巾打湿简单的擦一下,免得哗哗的流水声被村民听见,从院子外面观察就是这个院子未住人的感觉。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学法,有时一天我们可以学一遍《转法轮》即学九讲,那样的学法环境为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得当时有一对夫妻年轻同修,听说在当地有很好的工作,但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来到了北京,每天出去找外地来京无处居住的同修,在当时的恐怖环境下,风险是很大的,但他们每天做的很坦然,无声无息,当时全国各地大部分省份都有大法弟子来京了,宁夏当时还没有,那位妻子同修依然决定去银川找当地的同修,在临走的那天,我估计那时的银川气温已较低了,便将我的一件毛背心给了她以抵抵寒气。
记得有一天夜晚突然通知我们转移。我们二十多人便悄无声息的踏着月色跟着协调同修来到了另一处院落,原来是又有外地同修来了,便将我们原住地让给了他们,结果第二天很早通知我们马上离开现住地,并告诉我们何时在何地等候通知安排,当我们离开村落时,突然发现村口停了很多警车,原来是昨天来的同修住地被破坏了,很多同修被绑架了。当时即使在周边农村也到处可见警车,我与母亲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便走小路穿小巷,后来找不到同修了,我与母亲坐在路边商量着当晚的落脚地,因为当时的情况我们都没带身份证出门的,最后决定若找不到同修我们就选择远处一片齐腰高的枯萎的杂草,作为我们晚上睡觉的地方了。当时饿着肚子听着路边居家的炒菜声,难免勾起对家的怀念,但我们知道即使有再好的家庭条件,当师父与大法蒙冤时,我们在家的心也是不安的。后来我将母亲安排在一家餐厅,我又出去寻找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找到了同修,那个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谢谢师父!
后来我们经常与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都能接触上,在那个环境里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怕心、自私,协调同修经常组织同修们交流,经常有同修踏着月色、就着月光到我们住处交流(为了安全晚上从来不点灯),我们也外出去其他地方与同修交流,那段时光虽然条件很差,但对我们全国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返乡
在北京郊区住了一段时间后,我觉的我也应该回当地与同修交流一下,将北京的情况及自己的感受告诉同修,当我作出这个决定时,我看出了母亲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欣慰又担心我的安全(那时还不知否定迫害),我踏上返乡的路,回到家乡与同修们交流后,我便决定再次進京。当路过我家楼前时,我望着自家的窗户,心里对丈夫说了一声:“对不起,我暂时还不能回家!”(为避免麻烦我没让丈夫知道我回来)。当姊妹再次送我進京时,心情也是复杂的,既不想让我走,又知留不住我,又担心我的安危,她请我吃了饭,我便踏上了旅途。在车上半夜查票,当时对去北京查得很严,当查到我的座位时,旁边几位去河北某地的人与乘警说:“我们都是一起去某地的。”于是乘警就没过多的追问,但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保护弟子!
到了北京后進站口警察对進京人员查的很紧,每个人都核对身份证及车票,我在师父的点化下通过另一通道顺利出站,并且在车上还结识了另一位同修,到北京后我便去离京时居住的农户寻找母亲,可当我到村口时发现农户门口停有警车,我马上返回到村边一小卖部一打听,知道农户家被警察抄了,此时的我不知母亲的下落及安危,但我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呆了,便与结识的同修一起离开了此地。我联系了协调同修,同修将我们接到另一处,在后来的辗转中遇到了原来与母亲一起在农户家居住的同修,问起母亲的情况,他们说在警察進农户家之前他们已从后门离开了,后来就与母亲分开了,所以母亲的下落他们也不知。
后来来北京的外地同修越来越多,我们不断的结识各地同修,大家诉说着“七·二零”后各地的情况,开始出来的同修身上带的钱几乎不多了,后来来的同修主动在经济上承担大部分支出,在那个环境下,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大法使我们比家人还亲,有人负责采购,有人负责做点简单的饭菜,有人负责联络其他事。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当听到江魔头与法国记者信口雌黄诬蔑大法时,我们毅然决定去上访,向政府澄清实事,当晚我们将居住的农家收拾干净,三三俩俩的结伴来到了天安门……
结语:
因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有很多事情已记不太清了,但我相信当时全国大法弟子的所言所行,历史在清清楚楚记载着。现在每当我听到“天安门广场你可曾记得”、“烛光”等歌曲时,总是禁不住流泪,当年的一幕幕不断的闪现在眼前,今天也借明慧一角问候一声当年的同修:“同修你们都好吗?想必你们一定精進的走在各自的修炼路上,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共同精進,圆满随师还!”
叩谢恩师!
感谢同修的付出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