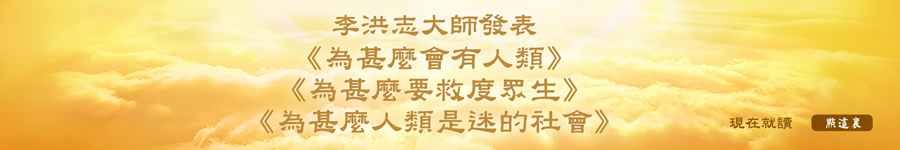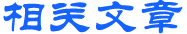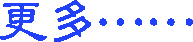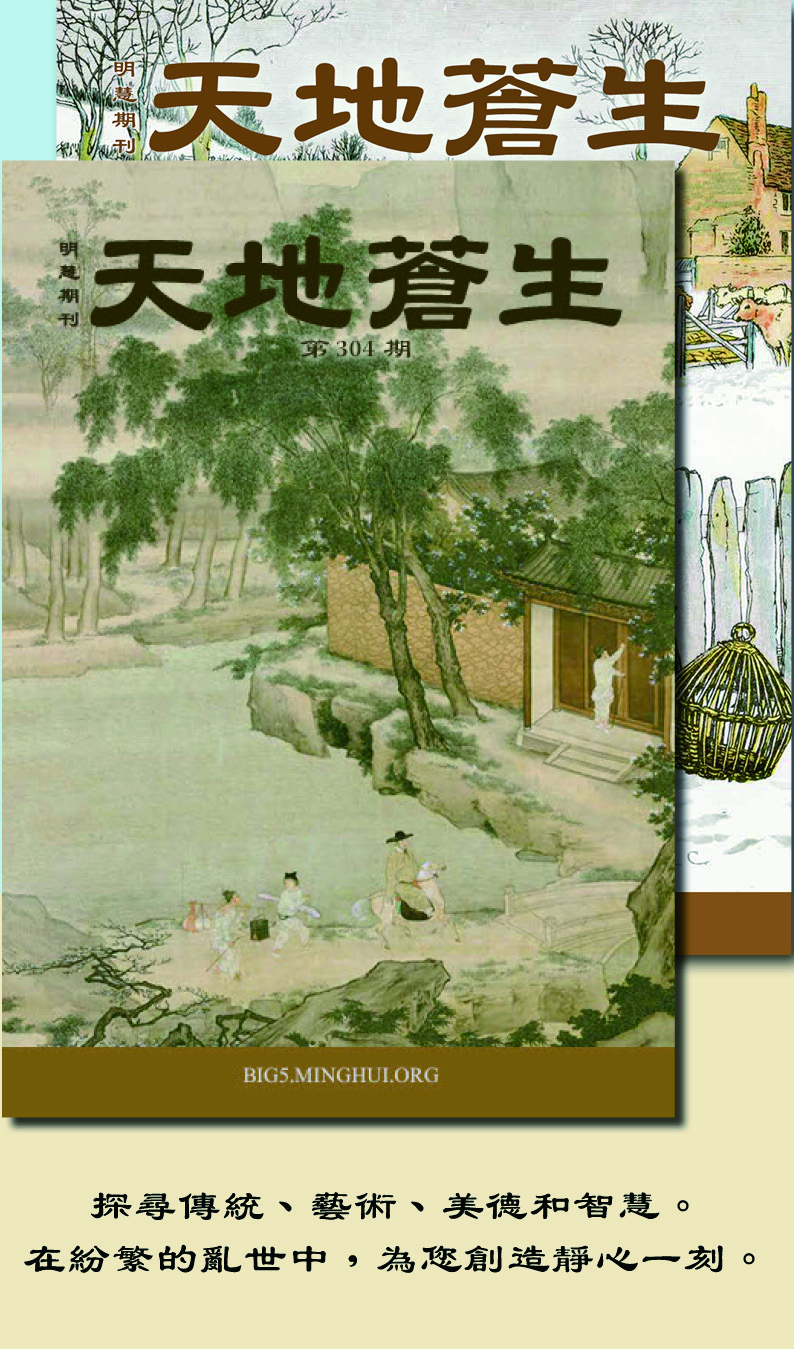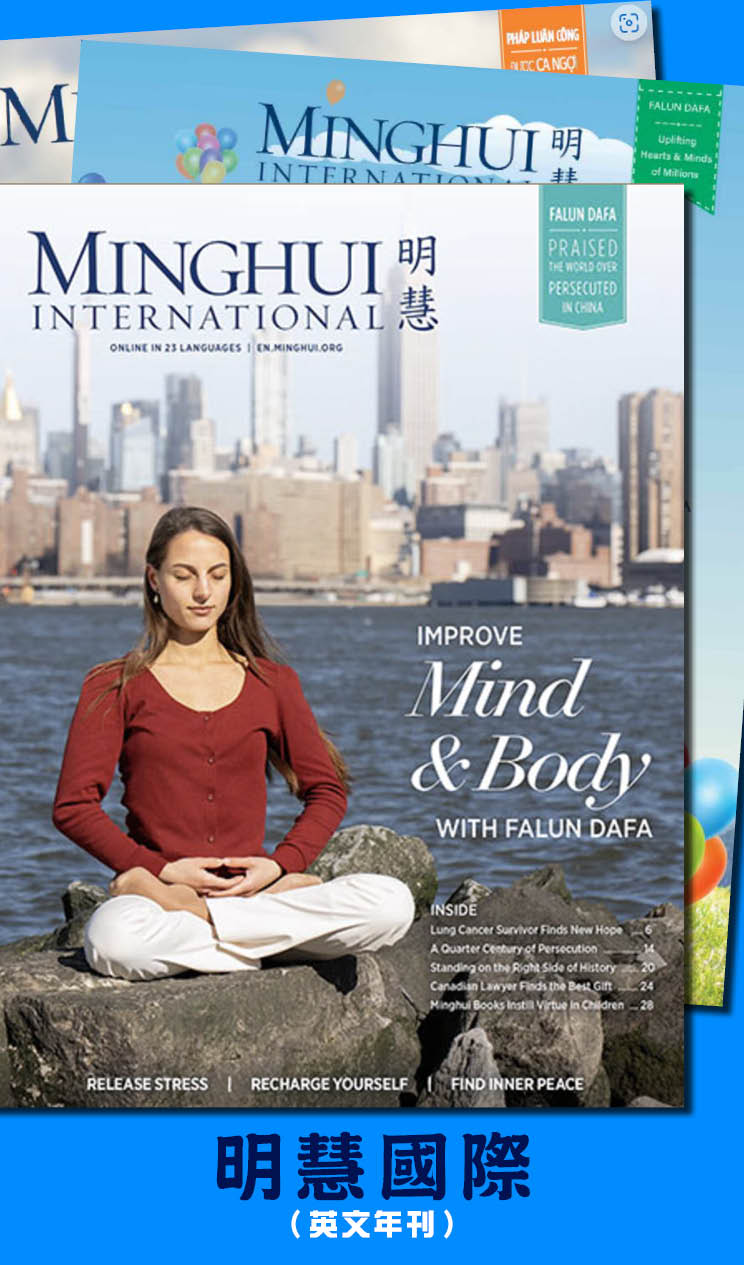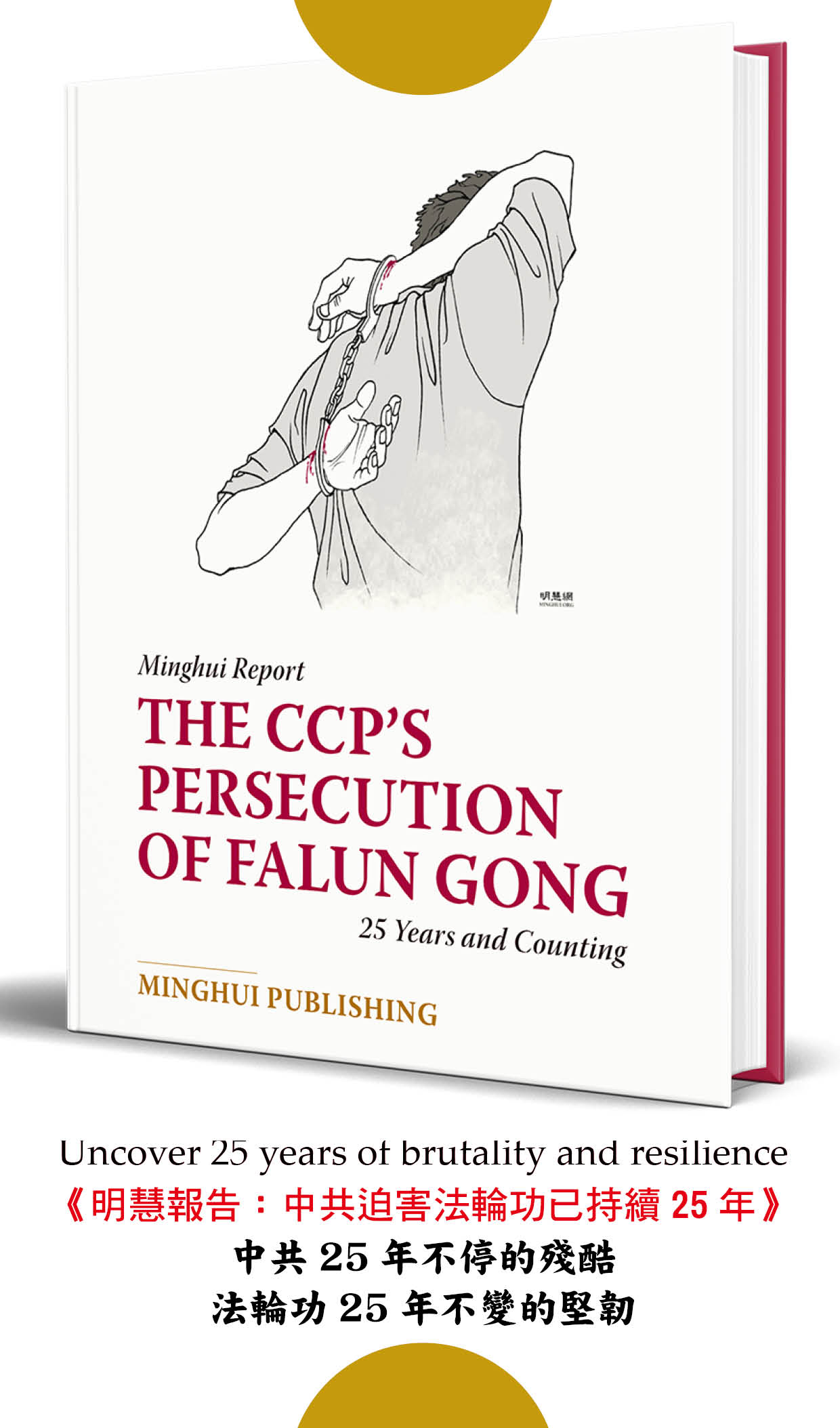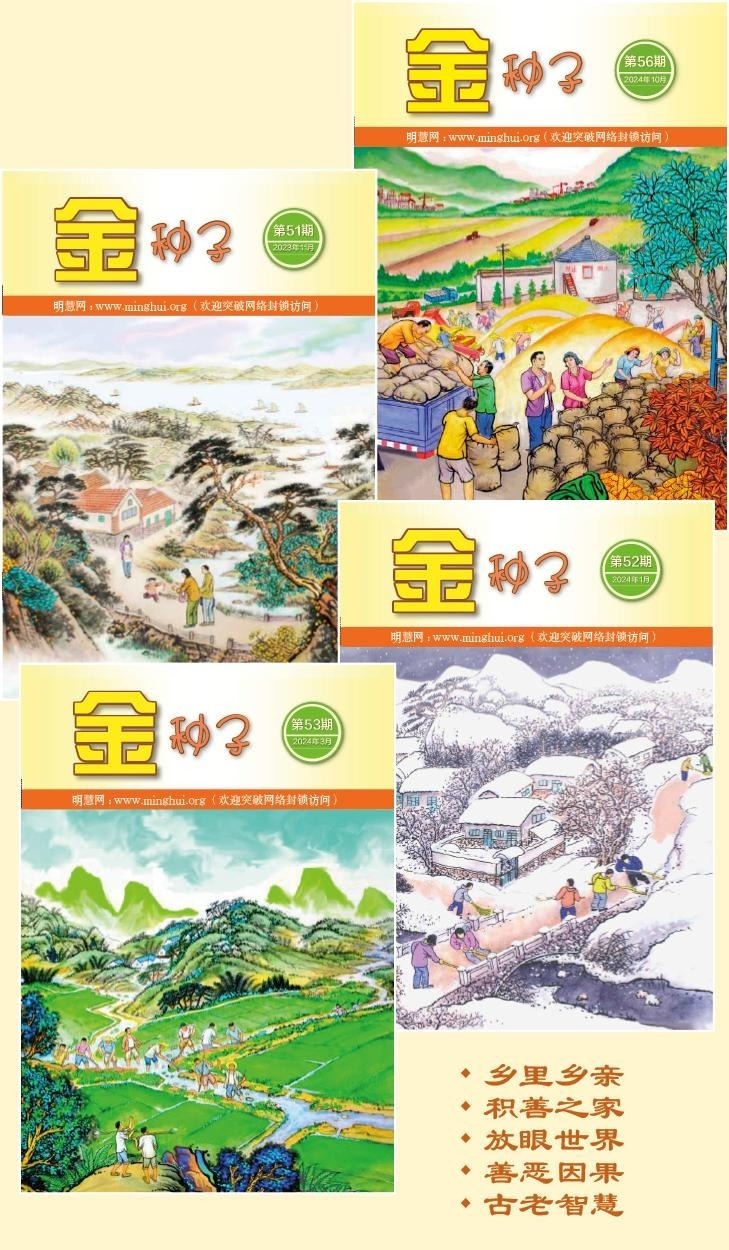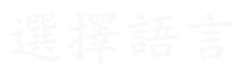河北保定市善良妇女孔红云遭受的迫害
下面是孔红云女士诉述她的遭遇:
我叫孔红云,二零零六年底第一次翻阅大法书,但我认为他就是一本普通的教人怎样做人的书,当时自己开诊所也没时间看,就放下了。在二零零七年,我诊所出了一次事故,当时感觉天要塌了,不知该怎么办,我把诊所关了七天,这七天我在家,拿起了大法书,一下走了进去,知道原来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因缘促成的,不是自己想怎样的。我一下释怀了,从来没有过的快乐踏实充满了我,但也不懂什么修炼不修炼的,只是觉的大法能净化人,怎么净化不懂,就喜欢这净化。
修炼后,我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我在棉纺厂42号楼开诊所,修炼大法后药品价格一降再降,周围居民都去我那里,说我价格便宜,态度好。在教育孩子上(我离异自己带孩子),有时孩子不听话就想发火,可这时想起师父说的,我就理顺一下自己的思维再去说。我与我母亲很少能谈得来,她说什么我都不爱听,心里也知道不对,可有时就是忍不住。学法后我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做事先考虑别人,我想一定要改变,有一次我母亲没完没了的数落我,开始我就忍着可后来实在受不了心里难受的都顶到嗓子了,这时突然想起我师父说的法,我一下忍住了,这时我母亲很奇怪的看着我说:“哎,你今天怎么没嚷我,”我笑着对她说:“妈,你看大法好吧。”
我沐浴在大法中,从未有过的幸福踏实,可就在我刚刚归正自己,真正做一个好人时,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保定依棉派出所却绑架了我,枉判了我三年,当时我女儿8岁。
从监狱回来后,看着我女儿那瘦小的身材,想起在监狱那个可怕的梦,梦见女儿被打的浑身是伤,来监狱找我,一进屋就晕倒了,我一下惊醒了。女儿怕我伤心,从来不提她的事,后来一点一点才告诉我,孩子在亲爸后妈那也承受了一般孩子无法承受的磨难。
我从监狱回来,一切都变了,诊所也关了。我想干点什么呢?学学摊煎饼吧,能见现钱,还能照顾孩子。我在保定盛兴路西口卖煎饼,可好景不长,在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上午被保定高开区贤台乡派出所六个警察入室绑架,并非法拘留十五天,十三岁的女儿放学后无法进家门。
二零一二年三月韩村派出所又非法拘留我七天。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我在保定农业大学里讲真相,发资料,被一个人构陷,南关派出所把我绑架,后来强行带我去体检,然后把我送拘留所,关押了五天。
二零一二年七月我原单位(贤台卫生院)与马纺卫生院归高开区管理,我们共有十几人按公务员从新分配,可因为我炼法轮功,别人都给安排,就不给我安排,高开区公益局说:“如果你转化了,写了四书,我们就接受你,给你工作。如不转化无限期延长。”后来袁局长说:“你哪怕骗骗我呢?”这显示出他善良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他的无奈。我们大法第一个字讲的就是真,师父让我们说真话办真事,我怎么能说假话骗人呢?再者如果善可以向恶屈服,还有善恶之分吗?如果好坏可以被暴力颠倒,强权左右,人类所有的价值将以何为基础。
二零一二年九月八日,我与陈秀梅一起去东贤台她亲戚家,在回来的路上,被贤台派出所警察截住,强行带到贤台派出所,在没有任何口供下,要非法拘留我们,因体检没结果拘留所拒收,他们没办法在回来的路上把我们放了。
回家后第二天去要我的电车,派出所没人。第三天又去,一警察(好象一副所长)说:“给你,你叫陈秀梅一块来,在我们这放着还麻烦呢?”我说:“你不就要给她钥匙吗?你给我,我给她不就行了?”“那不行,你们两个人的事,应该一块来拿!”我想了想,就去叫陈秀梅,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这是在欺骗我。
我与陈秀梅去了后,他们把我叫去让签字,可根本就没签什么字,却强行把我带上车,上车就给我戴上手铐,他们先把我拉到朝阳分局,又到保定市公安局,后又去高开区公安局。我一直喊大法好,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后来他们把我放了。回来后去找陈秀梅,可家里一直没人,我以为去她女儿家了,可后来才知道已被非法劳教。
十月二十九日晚我去贤台村,被一直跟踪我的车截住。他们又把我带到贤台派出所,后又到韩北派出所,在那呆了一夜。第二天韩北又把我带到康庄路洗脑班,在那非法拘禁了我两天,其中有一人(现不知叫什么名字)拿电棍电我。
回家后我又去要电车,他们要我签字,我拒签。他们又提出要电车发票,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日下午又去,他们说办事人没在,让我三号上午去。
回到家我母亲说:“派出所来了好多人,让搬家,明天下午两点之前搬清,还抄走了我好多东西,把网线也扯下来。”我母亲七十多岁,哪见过这个?把她吓坏了,一夜没合眼,早晨起来有点头晕。我想先让她回我哥那吧,因下午他们来不知会干出什么,我母亲怎承受的了。
十一月三日中午外边下起了雨,两点钟时,片警苏锦河(属新市场派出所管)带房东过来,苏锦河说:“怎么,今天搬不搬,不搬换锁,就因为你炼法轮功才让你搬家的,还有你孩子,我们还没找她学校,让她退学。”他们还要搞株连迫害,我说:“搬家可以,容我几天时间找房子,再者你们昨天来是让我搬家而不是抄家,把抄走我的东西送回来,我就搬。”
后来苏锦河打电话叫来藏飞、焦永章两人,把居委会也叫过来,他们叫来换锁的,强行把我家的锁给换了,苏锦河、藏飞他们强拉硬推把我从我家里拽出来,外面下着雨,后来他们又强行把我拽上他们的车,说送洗脑班,到七一家具城门口,他们又强拉我下车,焦永章说:“让她下车,她不怕雨淋,别脏了我们的车。”我无法容忍他们这种强盗行为,有种从未有过的屈辱。
我打车去了他们派出所,找他们白所长,可他说不管,他指着苏锦河说找他,可苏锦河是听他的,他是领导。他们这种违法行为我不能接受,房子虽然是我租的,可也是有合同的,我是有使用权的。他们整天讲要社会稳定搞什么维稳,大家想想,每个家庭是组成社会的一个粒子,家庭的稳定才会使社会稳定。那么大家细想谁才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共历次运动,谁是引起动乱的根源。
后来臧飞过来我就给他说,他不但不听还拿报纸堵我的嘴。我就在他们派出所呆着,他们把我家锁给换了,我能上哪。后来我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可臧飞一看我出去,却赶紧把大门关上,不让我进去,外面一直下着雨,我说你们把门开开,这大晩上我上哪去,我没地方去,可他们就是不开,后来有人要进去,我就跟上,但那白所长却使劲把我推倒在地,只要有人来我就跟着进,可每次都被他们推出来,每次臧飞都积极参与把我推出来。我听说抄走我的东西就是他干的。后来一出警警车回来,我再次跟上,他们却拿电棍电我手,我左手中指无名指都肿起来鲜血直流。
我就这样在他们门口淋着雨,当时浑身湿透又冷又饿,面对这些麻木的人,内心感到一种悲哀,我实在不愿再面对他们,他们已经人性全无,就是动物还有怜悯之心。他们利用手里这点应该说是神圣的、拿着纳税人的钱、应该维护人民的这点权力,却紧跟着邪党反过来迫害人民。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邪党历次运动都能得以成功,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害死我们那么多同胞还能苟延残喘到今天,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七日,我又一次被保定市南关大街派出所绑架,派出所没有通知家属,也没给任何手续,把我劫持到保定市拘留所。女儿报警后才知道是被南关大街派出所恶警绑架,和家人去派出所要人,五天后他们放我回家。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保定易县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易县塘湖派出所绑架,所长黄建良拿电棍电我手和脸,晚上几个人问我叫什么,我不说,他们把我拽到墙角,拳打脚踢,后来把我铐在暖气管上。半夜把我送进拘留所。我绝食抗议,十月二十日,家里去要人,他们把我放了。
二零一四年一月,在保定市竞秀公园门口被不明真相人举报,再一次遭保定市新市区竞秀公园派出所恶警绑架,当时出了一非常不正的念头,老被抓了真丢人,能没有声息的放我回家就好了,被这一念带动忘了自己的使命,后被他们强行送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不给它干活,同一屋几个人围攻我,后来好象队长过来她们才停手。我绝食抗议,被灌食,后来又给插管好象一个月左右,我拔出来,她们又给灌食,几个人按着我,还有抓脚心的,有拿勺子翘嘴的。
后来我的腿不知怎么站不起来了,上厕所时得让人把我拉起来了,我自己起不来,而且大便失禁,我不能自控,记忆力混乱,减退,还有炼功动作也想不起来,现在分析觉得我是在看守所被下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
这次我被非法判了四年。到石家庄女子监狱后,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犯人就拿厕所抹布堵我嘴,她们带我去体检,我就见到谁就给讲三退真相。后来她们把我分到十三监区,是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监区,在内心矛盾中我把四书已经写了,可是总觉的师父有着无量的慈悲,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所以让我写别的我就说什么也不写了,她们就开始打我。当时内心很矛盾,她们以为我又转回去了,因为我嘴上一直说大法好的那面,真善忍是没有错的。她们把我拽到厕所打,一人坐到我身上,揪我头发,把头拽起来,另一人打耳光,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有一天那人用脚尖踢我的腿,踢大腿内侧,用手打脸(这个人很邪恶,专踢人大腿内侧敏感地方),我就感觉鼻孔往外流东西,我不知是打出血,这时她就拽我上厕所,我就是不去,鼻孔一直流血,我用手擦,才知是血。一小队长过来说,你们炼功人出了那么多问题(其实中共造的假资料),你认为好,那她们呢?我不知该怎么办,想我这样是不是也不负责任,那些人呢?于是就又接着写了,可写着写着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把以前写的撕了扔掉,她们就罚我站着,我想站着就站着,不让写就行。后来我就盘腿坐着,她们发现后把我铐在窗户上。
后来又来一唐山的叫党凤玲(邪悟者,邪悟后很邪),我从前认识她,我不认同她的说法,她就把我拽到厕所里打耳光,打一下问一句,打一下问一句,让我认同她的说法,我就不认同,她打我我就喊大法好。她每次都是等监区人出工了,就开始变着样的整大法弟子。她拿来墨水在我脸上画,说你在外面就给人墙上写,看我写你脸上,看你什么滋味,我急了,把盆给她扔了,有一次等人们出工后,她说你不喊吗?今天我让你喊个够,她就动手了, 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后来也许她打累了,就用两个手掐着拧我前胸和胳膊内侧,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前胸都没好地方了。
就在下午,队长交接班时,我把前胸拉开让队长看,曝光她的邪恶,却又招来党凤玲和另一个人一顿打,她们两个人把我打倒,党凤玲坐在我身上一下一下的往下压。
监控我的共三个人,党凤玲几乎天天打我,有时两个人打,另一个人拽着我的手不让我动。有一次我看到我右眼下面被打的都是黑色的。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变了,说我们活跃活跃气氛,看电视剧吧,锻炼锻炼身体,在后来把她调走了。
后来把我带到八监区,有两个人专门跟着我,我到哪她们都跟着,不能单独上厕所,限制与别人说话。我就不想让她们跟着,想摆脱她们,她们干活的时候,我不跟她们说,我就上厕所,她们有时生气了就招来一顿拳脚,我不管她们怎么对待我,我就是不想让她们跟着。后来我听见她们与别人说,其实孔红云真的很善良,可我们没办法,是她的护监,不打她怕队长找我们麻烦。
过了段时间,我想炼功,一个队长把我铐起来,第二天又把我吊起来,三个队长,其中两个拿电棍轮番电我,另一个人只动手,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个是我们包组叫什么忘了,一个姓翟,一个好象姓陈,陈只是动手。
有一次我绝食,收工后,队长带我去灌食,灌完刚走出医院门口,队长让两个犯人,一边一个拽着我的胳膊,她拿电棍从我后背开始电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又电前胸,她让两个犯人把我手举起来电我手脖子,我就喊,后来不知为什么她好象有点害怕了收手了。
还有一次,犯医焦红霞非常邪恶,在车间,她把我的两手两脚捆住,把嘴用胶带缠上,我想上厕所,她不让去,我尿在裤子里了。我在绝食抗议迫害时,焦红霞用勺子撬牙,牙齿被撬的变形。
还有一次,我绝食,犯医焦红霞给我灌了很多盐,浑身烧的不行,我就用凉水往身上浇,有一天是包组队长带我去走到食堂那儿,她让犯人给灌食里面放盐,让多放,犯医说,那样她就会烧的难受了,包组说烧她烧去吧。
从石家庄监狱回来,我一无所有,孩子上学这几年,欠了很多债务,我没有办法,就去高新区找我以前的工作,现法律有这方面的规定,判刑出来的半年内每月给2300元最低生活保障加三金,或给安排工作。我就去找他们,这本来是他们应该做的,也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可他们却一推再推。没办法,我就在区政府门口给进进出出的人们讲真相,被门卫构陷,被高新区派出所拉到保定清苑拘留所非法关押了四天,过程中我一直绝食喊口号抗议。
从二零零八年三月,我多次的被绑架关押,两次被判刑迫害,我做了什么?只是想真正做一个好人,把自己的人生走正。我离异自己带孩子,女儿这几年也跟着承受了一般孩子无法承受的魔难,母亲这几年也是经常以泪洗面。
法轮功学员以真、善、忍为标准,无条件找自己的不足,对稳定社会、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修炼法轮功 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的诚实、善良、宽容、忍让遇事向内找,先考虑别人,先他后我,与人为善。
中共“假、恶、斗”自建政以来,周期性的政治运动,都是利用我们中国人来害中国人。文化大革命,你斗我、我斗你、孩子斗父母、学生斗老师、夫妻反目,“六.四”镇压大学生,把手无寸铁的学生轧成肉酱,为了谁的稳定?它政权的稳定,而不是百姓安居乐业的稳定,让中国百姓在颤抖中屈服。对法轮功的迫害最为惨烈,因迫害的是人的良知、人性的根本,所以没有比迫害良知更邪恶了,通过迫害人的肉体及侵害各方面权力而达到毁灭其灵魂为目的。
中共统治的稳定是建立在毁坏我中华人民的人性的基础上。英国政治家爱德蒙·伯克说过这样一句:“邪恶获得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细想,其实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而得以成全呢?许多人觉得中共迫害法轮功和自己无关,这是错误的认识。在这场善与恶、正与邪的较量中,沉默其实就是怂恿邪恶,沉默就是邪恶的帮凶,因此保持沉默,保持所谓的中立,其实质是帮助了邪恶,助长了邪恶的气焰。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就是一种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