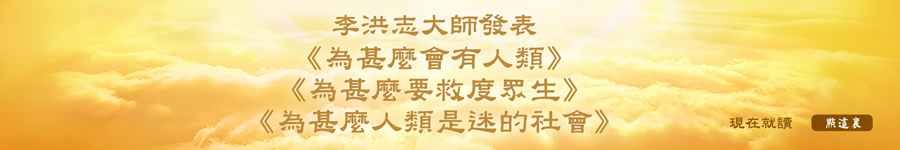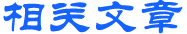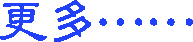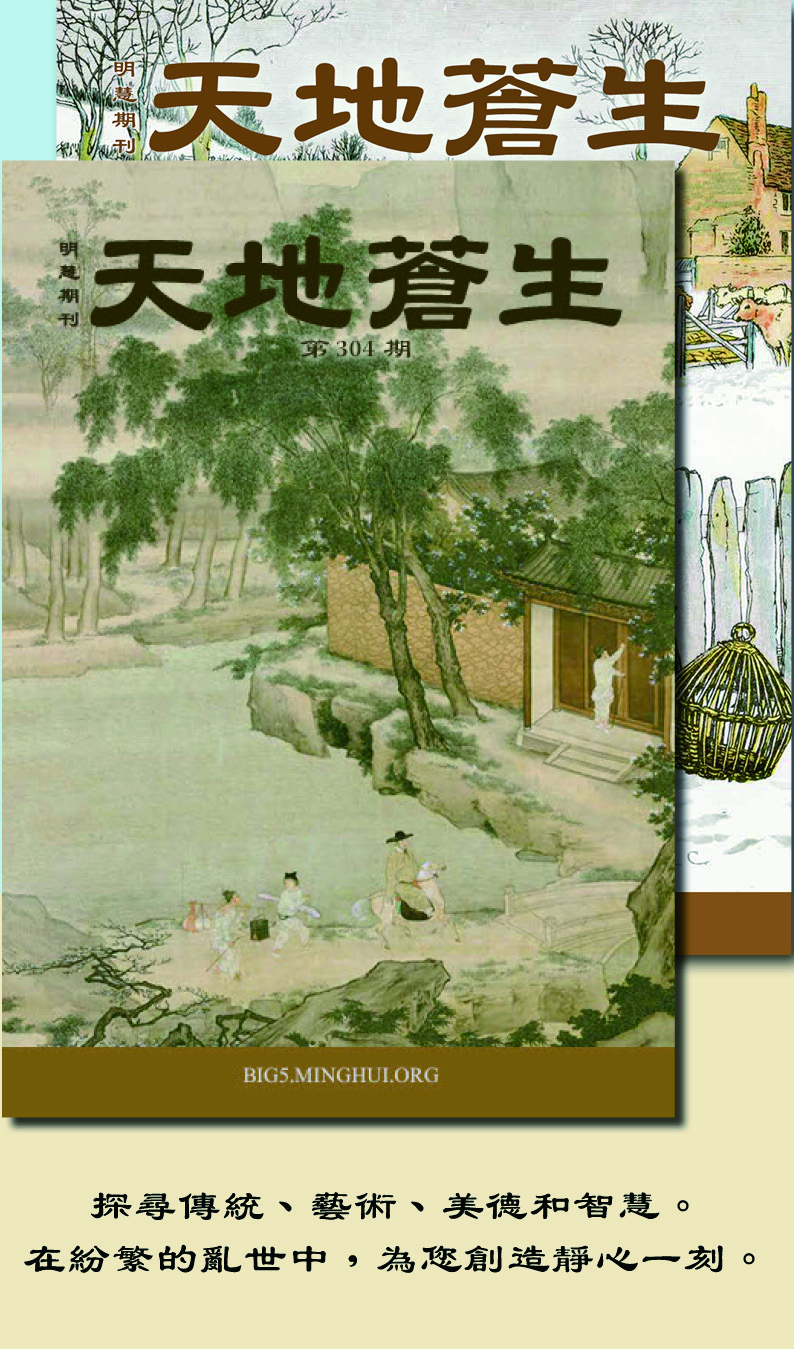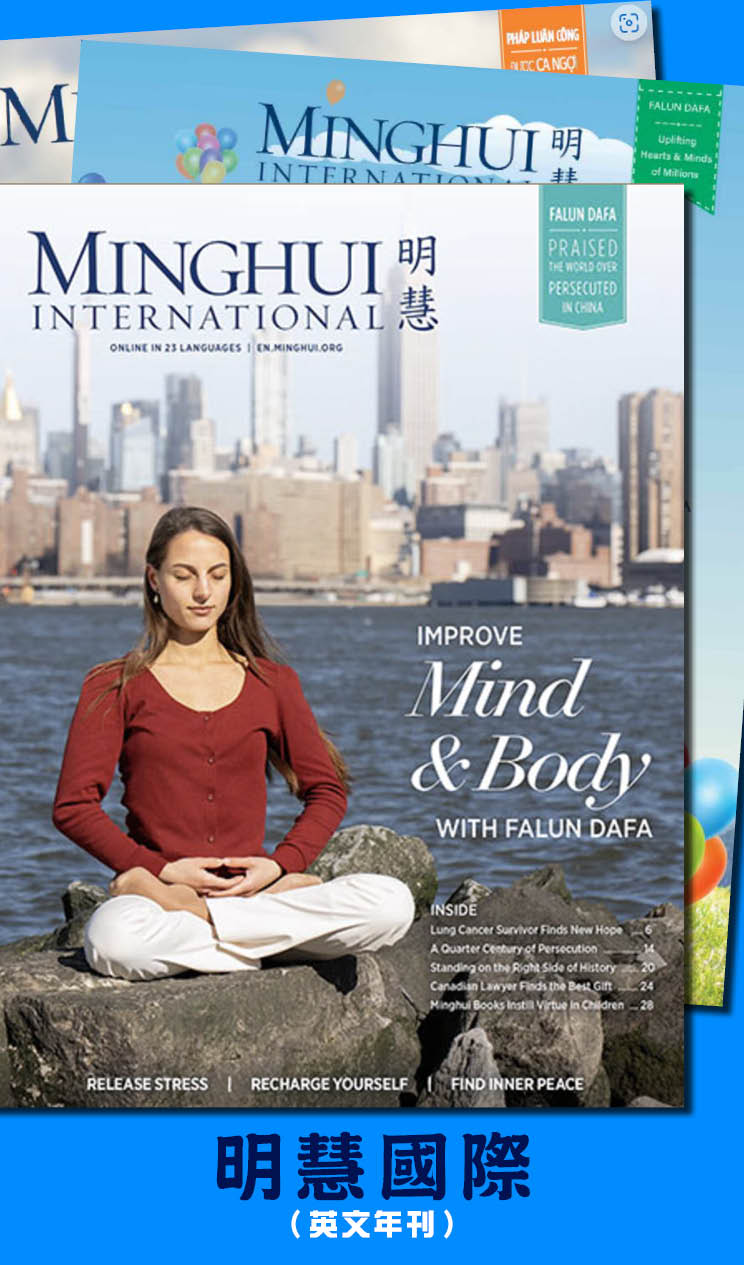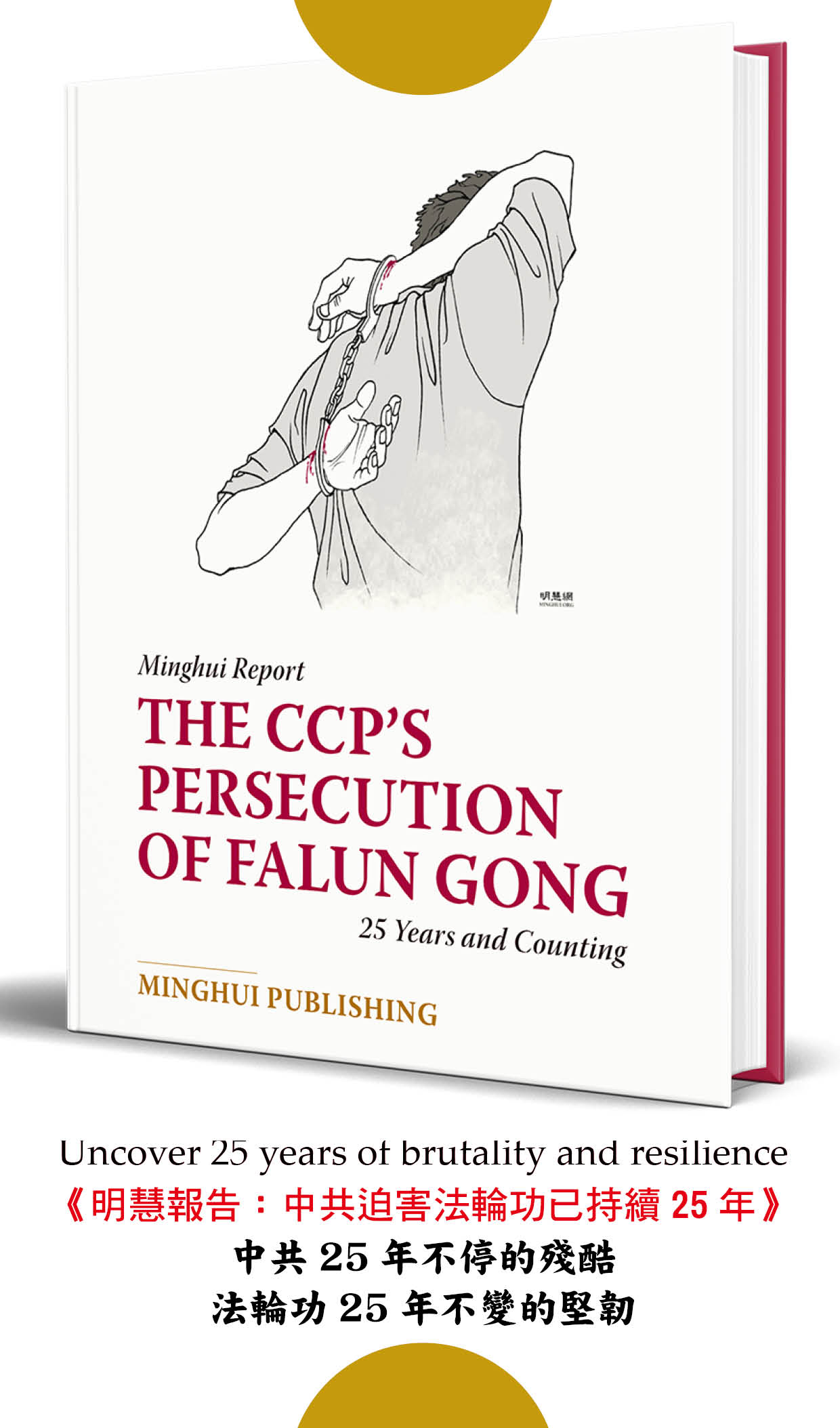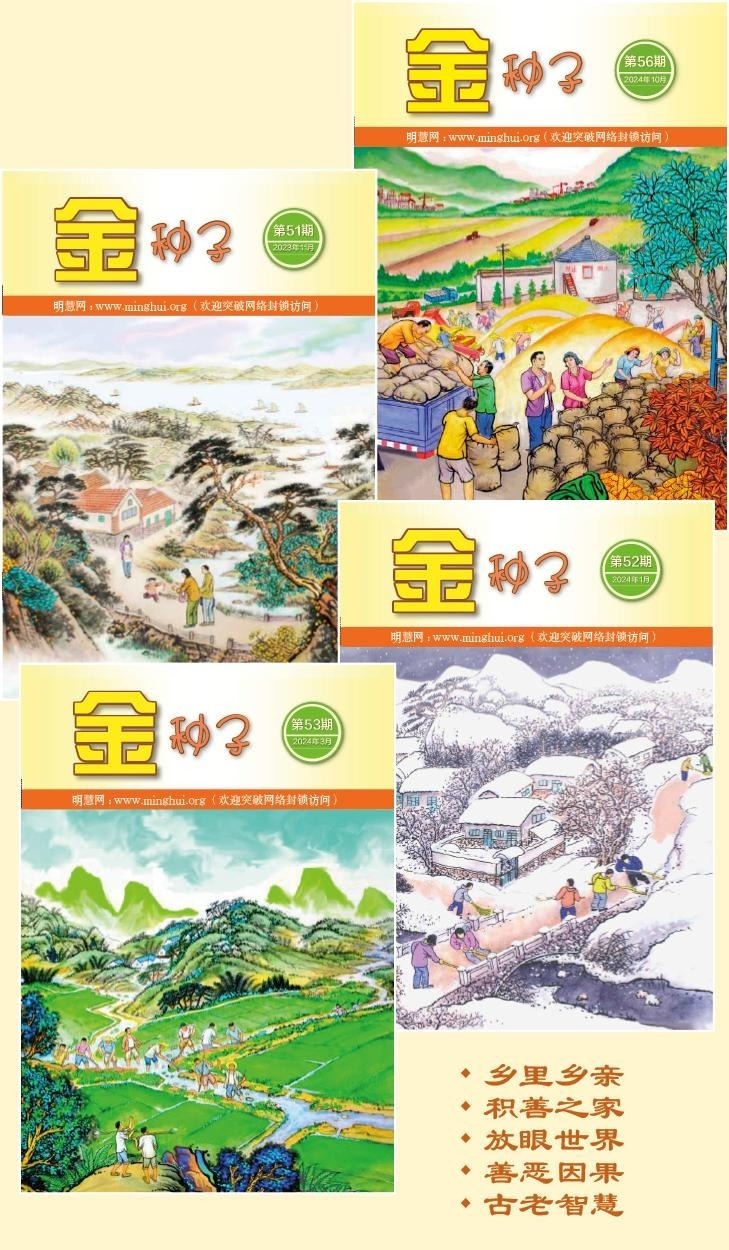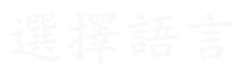河南省唐河县原政府干部张明贵控告元凶江泽民
今年59岁的张明贵坚持修炼法轮功,共被绑架三次,第一次被刑事拘留22天;第二次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转入行政拘留所监视居住6个月,又被劳教两年;第三次被判刑三年。在被关押期间,他屡遭酷刑折磨。
以下是张明贵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修炼法轮功,我身心受益
我于1997年9月27日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和住房的困难,再加上工作上的不顺心和家庭矛盾的不断升级,使我变得对人生暗淡,工作消极,整天和同事们下村工作就是酗酒,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整天昏昏沉沉,全身无力,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甚至有想出家当和尚和轻生的念头,总觉得人生渺茫,活的太累。
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桐寨铺镇粮管所办公室主任罗久河介绍,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功,通过学习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一书,使我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全部破解,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等许多问题。从此我的人生观全部改变了。
我吸烟、喝酒二十多年了,从修炼的第一天开始就全部戒掉,包括赌博恶习和所有不良习惯都全部戒掉。我修炼大法后,我家的小吃店生意越来越好,生活和经济上也富裕了,又在城市中心买了160平米的楼房。
家庭和睦了,我工作上也积极认真了。我妻子见人就夸:“俺老张修炼法轮功后,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好人,镇政府的干部们都公认老张是个好人,镇政府只有俺老张才是清政廉洁的好干部。”
我处处事事按照真、善、忍去做,遇事向内找,不争不斗,把名利看的很淡,买东西时经常遇到卖主多找钱和少算几十元钱我都主动归还。2002年9月我捡到了1000元现金和身份证并主动找到失主归还。在工作中能得到别人给的好处及现金,我都一一拒收。
修炼后,使我变的乐观向上,宽容善良、勤劳,身体变的非常健康,整天一身轻。修炼18年至今从来没有得过任何病,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我今年59岁了,我觉得比我修炼前40岁时身体还棒。别人都说我又年轻,又精神。
第一次被绑架,遭奴役迫害
正当法轮大法给我带来幸福美满的时候,突然在1999年7月22日深夜2点左右,在我什么都不知的情况下,桐寨铺镇派出所警察和唐河县公安局政保科的4个警察和一个保安闯入我所在镇政府住处把我从熟睡中惊醒。
警察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两个警察就每人各拧我一只胳膊,另几个警察在屋里搜查。搜走了我的录音机和所有炼功音乐磁带及所有法轮大法的书籍。当时都把我妻子和儿女们都吓傻了。
他们把我押上了警车拉到了唐河县公安局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警察们说,只要你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就放你回家,我说,“不写,我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强身健体,我没错。”
后来他们就把我关进了县刑事拘留所,并强制我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11点做奴役苦工,做医药上用的针剂纸盒,每天吃的都是稀粥和冬瓜汤,冬瓜不削皮,冬瓜皮上带的都是沙子和泥土。吃不饱,蚊虫咬,闷热的监舍,超强度的苦役,使我身心都受到了不同的伤害。共关押我22天放出。
第二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
回家后还经常受到镇政府和派出所的骚扰。由于政府对我们师父和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待遇,2000年6月大概是27日,我和本镇同修毛奇和毛长青正商量准备去北京天安门请愿,被人告密诬陷,又被唐河县公安局安保大队的李炳山科长和另两名警察把我绑架到了县看守所关押迫害,迫害的遭遇还是超负荷无偿做奴役苦工。关押一个月后又把我转入到县行政拘留所关押了六个月。
在这关押的6个月当中,我真是过的是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夏天又热又脏,成群的蚊虫穿窗进监舍,晚上被咬的奇痒难以入睡,冬天大风穿窗把雪花刮进监舍,冻的彻夜难眠,饥寒交迫。
警察多次来找我谈话,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就放我回家。我说:“我修炼法轮功受益很大,我炼炼功就是想有个好身体,按照真善忍去做个好人,我不能昧着良心去说不利于大法的话。”
由于没有配合警察的要求,他们每天让其只给三小勺稀面粥,折合一两面粉,半月才解一次大便,六个月下来,被关押的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饿的皮包骨头,整个人都脱了像。我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坚持炼全五套功法,有时间炼第二套功法抱轮一站就是两个小时,我不但人没有消瘦,而且脸色白里透红,警察们都觉得有点奇怪,都说我越饿越年轻了。这就是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由于我在关押期中,我绝食抗议对我们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写了一份反映拘留所的伙食问体。所以警察为了报复我,就冤判了我两年劳教,县组织部又下发了关于开除我党籍的文件,(正好,我退出中国共产党)在拘留所关押的6个月还不算劳教刑期,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一至三个月的都算上了劳教刑期。冤判我劳教后,给我戴上手铐押送到南阳市遣送站关押15天后,又转押到河南省(许昌市)第三劳教所进行迫害。
在劳教所被迫害期间,主要是给洗脑转化、灌输诬蔑法轮大法的谎言,然后是让我们长期超负荷的做奴役,主要是做假发。
我被解除劳教回家后,桐寨铺镇政府书记杨新亚不让我上班,并扣发了我所有的工资。我只好在自家的小吃店帮忙。
我记得是2002年11月的一天上午8点左右,桐寨铺镇派出所三个警察开着一辆警车堵住我家的小吃店门口,说让我上警车跟他们去一趟。我一听他们又要绑架我,被我严词拒绝,趁他们一不留神,我急速的从店里屋的房顶上的一个小洞钻了出去,然后从平房跳下地走脱了。从此我就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
我遭受了迫害也连累了家人。我母亲整天为我担惊受怕体弱成疾;我岳父因为我气的得病早逝;我妻子和女儿整天以泪洗面;儿子在学校受到同学们侮辱,在他上初一那年他母亲就让他停了学,在小吃店帮忙。
2002年我女儿放暑假在我家小吃店经营,被当地一地痞流氓羞辱未遂,又一当地地痞直接闯入我家店内就解小便,另有一名卖鱼的地头蛇叫李老三的把我家小吃店砸个稀巴烂。由于受人欺负,再无法经营,我妻子只好把店转让了。我儿子14岁那年就去北京市当了保安。
第三次被绑架,被殴打折磨
2004年10月6日,我在北京一家公司打工,利用休息时间,我骑自行车,带着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去北京通州区农村讲真相。当我给了一名女青年真相资料后,她悄悄的打手机报了警。
警车来后,拦住了我的去路。两个便衣飞快的抓住我的双臂向后拧,另一名警察凶狠的用飞脚猛踢我的双腿,大约半个钟头后,把我按倒在地,警察把我裤子拽掉后,并拉我双腿使我后背着地,被石子划破流血。但仍无法把我弄上车。警察又打手机,叫来一辆警车,他们用绳子捆住我的双腿,又用手铐铐在腿上的绳子上,使我整个身体成了四十五度。
他们把我拉到当地派出所后,我连续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凶狠的打我的脸,拿电棍电我全身,电我嘴不让我喊,一直到半夜又把我送到通州区派出所进行迫害。
强行给我检查身体时,我不配合,并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狠劲打我的脸,用双手狠掐我的脸,打的我顺嘴流血,我躺在地上闭着眼一动不动,他们才停下。两个便衣把我抬到看守所的登记室。看守所的一名警察命令两个便衣把我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并抢走了我口袋中的400元钱,然后又把我抬进了一个监室里。
第二天,我开始绝食绝水抗议迫害,第三天狱警董亚新找我训话,我进他的办公室不喊报告,不抱头,不蹲下,反正一切不配合。警察就叫来几个恶人将我砸上了钩链,所谓的钩链就是手铐和脚链铐在一起成四十五度角,只能坐,不能躺。
到第四天我的双手都红肿了,恶警给我又戴了一个摩托车头盔。就这样持续七天,他们才把我放开。他们在给我插管灌食时,我还给他们讲真相。当他们阻挠我炼功时,我就连续喊:“法轮大法好!”继续绝食。狱警无奈的说:“喊法轮大法好喊的挺好听,你使劲喊吧,只要你吃饭,就顺着您”。
换看守所迫害
通州区看守所警察将我折磨的不象样了,也没得到我的只言片语。于2004年11月5日将我转送到北京公安七处,警察们让我签字我不签,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进监舍牢头让我抱头,我不抱,让我下蹲,我不蹲,他们就狠踢我的脸,打我耳光。我不按手印不签名,三个警察将我按倒强行抓我的手写。
零五年一月五日,狱警们又把我转回了通州看守所,四号监舍有个姓杜的号长,安排了三个恶人当打手,每天欺负同室的犯人。但从不打我,他们都说法轮功是好人,不能打。
通州区看守所环境非常恶劣,有句顺口溜“吃饭没碗,睡觉立板,水洗××,随时就会挨板”。吃饭没碗是叫没钱买碗的人先吃窝窝头,(窝窝头是玉米渣做的)不让你用碗喝水、喝汤。睡觉立板是监室地方小,在押犯人数多无法睡觉,号长就叫新来的人整夜站那值班,多数人被站的两腿、脚紫肿,站那睡着了也挨打,就是能睡觉的人身体也是立着睡。解大便白天限制时间,超过三分钟,号长就叫人往身上泼冷水,每天只能方便一次,还得统一到下午六点排队等待。号长让打手控制手纸,没钱交号费的不让你用手纸,叫你用凉水洗。晚上厕所锁门,每人各用个饮料瓶解小便,若谁闹肚子需要解大便,那就拉在自己的衣服里包着,等天亮起来再把大便倒厕所。多数交不起二百元号费的人,不但遭此凌辱,还要承受恶人用板子打臀部、头顶墙架飞机的酷刑。
二零零五年二月五日,通州区法院开庭对我迫害,法警给我戴手铐让我蹲下我拒绝,他们就用脚踢我双腿,强行给我戴上背铐,把手腕勒的很紧。上法庭时,两个法警每人架我一只胳膊,让我低头。一个法警用拳头猛打我的前胸数次,致使我右胸结一硬块发紫,三个多月后才消失。每当警察打我时,我就喊:“首都警察打人了。”我只要一喊,法警就不敢再打了。在法庭上,厅长说:“只要你与法轮功决裂,就不会判你刑。”我回答:“我无罪,法轮大法是正法!”
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五日,通州区法院强行给我发了非法判决书,强加于我三年刑期,我不服要上诉,但狱警不给我纸笔,无法上诉,我绝食绝水抗议共产党不讲法律,绝食第四天,狱警张伟和董亚新把我叫去说:“让你上诉,只要你吃饭,就给你纸笔。”我说:“你说话要算数,另外你们掏走我四百元钱得还给我,不然我就不吃。”他问我:“你又不知道是谁拿的,咋还?不过这钱真找不到,我私下给你,只要你吃饭,别再胡闹了。”他又说:“其实我这个人并不坏,只因我在六一零办公室上班,带队抓过你们法轮功,那也是工作,可你们就给我上了网,出于内心,我也不愿这样做,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你想炼自己在家炼就行了,干嘛要到处撒传单?你回去给你们的人说说,把我的名字去掉吧。”
我借此机会又给他讲了真相,他也认可,但他们说话是不算数的,只给了我纸笔,钱却不给我,我又绝食四天,最后晕倒。狱警们害怕了,把我按倒插管灌食,我不配合。最后他们说只要吃饭,钱一定给你,但只给三百元,你写个条子。我想先给三百元再说,我就写了条子,给他们一个台阶下,我先收回了我的三百元。他们还给了我纸和笔,我就写了一份向北京市中院的上诉书:“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无罪,我们给世人的真相资料讲的都是真话。江泽民才是人民的罪人,我要控告江泽民,把江泽民推到人民的审判台上去,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这是我在上诉书中写的片段内容。
我自此坚持每天炼完五套功法,狱警们通过探头看到我炼功就来阻止,我不听,继续炼。他们强行不让我炼,我就绝食,他们没办法只好说:“你炼吧,有本事,你把天炼塌。”
零五年四月五日,上午十点左右,北京市中院两个法官找我询问,其中一个暗示我说:“你当时拿的资料和光盘是去扔掉的吧,你只要写一个对法轮功的认识就好说。”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是做好人的,无罪,法轮功真相资料上说的都是真话,为什么不让讲呢?”他们只好按我所讲的记录了下来。当时如果我按他们暗示的去说,也许判不了刑,但我绝对是不能那样去做的。
零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院强行给我下发了非法判决书,维持原判。因此通州区开始给我照相,让我按手印,我都不配合,狱警们就找了几个彪形大汉给我戴上脚链和手铐,又把我按倒在地上,狱警副所长脚踩我的脖子,恶人掰我手指,并拿电棍往我手上电,强行画了押,
转押监狱迫害
零五年五月十七日,狱警准备将我送往天河监狱,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走出看守所,当天上午到达天河监狱后,狱警们强迫我体检身体,我不配合,狱警们就给我戴背铐,通州区派出所副所长骂我,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看守所恶所长骂人了”。
这个副所长气的脸通红,并指使四个彪形大汉的犯人把我按倒在地,强行抽我左胳膊的血,然后这几个坏人把我架到透视台上做透视,他们无法控制我上透视台,又怕我弄坏设备,野蛮的给我注射不明药物,恶警命令坏人把我抬到一边,等药劲上来再查。于是我就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狱警说药劲起效了,快把他抬上去。可当把我抬到透视台上后,我突然又迅速的跳下来,狱警说:“这法轮功,还骗人呢!”其实那药物对我根本不起作用。
中午一点左右,通州区将我移交给了天河监狱的一个大队。到那后,狱警长拷问我,我就给他讲真相,刑事犯人让我学规范报告词,还让我抱头蹲下,我都不配合。他们骂我,狱警指派一名大学生犯人包夹我,我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大法洪传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每天我什么活都不干。他们就让我从上午八点钟坐小凳子坐到下午六点钟。一坐就是21天。
转原籍迫害
零五年六月八日,正是天气炎热的时候,火辣辣的太阳晒的人们喘不过气,这一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防暴警成群结队,头戴钢盔身扎佩带,个个手持高压伏电棍“叭叭”乱响一片。武警手持冲锋枪,警笛响声震耳,那阵势真象是赴刑场一般。
狱警将河南籍将近二百名刑事犯人和我集合起来,命令所有在押人员抱头蹲下,我不抱头,恶警来给我戴脚镣,我拒绝不戴,一个警察就凶狠的往我下身踢去和猛踹。要不是正念的作用,我想真的就会失去肉身。我高声喊:“首都警察打人了。”这时来了一个带队的头来调解,并和气的说:“对不起,这是上级的命令,请你配合,我们是在执行任务,请你谅解”。我说;“我又没犯罪,为啥给我戴脚镣,那个警察还是首都警察哩,啥素质!脚往我致命处踢,想踢死我呀。”这个警察说:“委屈你了,配合一下吧。”后来踢我的狱警说:“就你这样,如果是前几年不整死你才怪哩。”
到北京西站时,其中一个狱警手持电棍“叭叭”作响,令我抱头,我就不抱,这名狱警说你真不抱?我答道:我又没有犯罪,就是不抱。他竖起大拇指说:真是好样的,佩服,佩服。
零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夜十二点多,到达河南省新乡市火车站,下车后,就有第二监狱的狱警来接站,他们同样逼我抱头,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我从没有给任何人抱过头。”他们没办法只好把我拉到了河南省第二监狱,关进了又脏又臭的禁闭室。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河南省郑州监狱一个姓窦的教育科科长来拉我,我一路上不停的给他讲真相。姓窦的对我发火,我还和气继续的给他讲。下午一点左右到达郑州监狱后,他们把我分到五监区。到这里后,没有见到一个警察,是三个刑事犯发号施令,检查我所带的行李,又搜我全身。检查完毕,把我带到一个监舍的小屋里与我交谈。我给他讲真相,他们表现的很和善,很家常。可到第二天他们就翻脸了。原来是派来给我洗脑的,一个是犯人头,另两个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
第二天早上有个叫安松昌,一个叫贾寅卫的恶人,把我带到一个很脏的屋子里,让我作三姿,即“站姿、坐姿、蹲姿”其中蹲姿最难忍,蹲几天后,能把腿脚蹲肿,而且蹲时还不让动,每天从早上七点开始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当然,我抗议不做,他们就打我。我和善的对他们说:我来到这里是冤枉的,希望你们不要迫害我,这三姿我都会做,我是当兵的出身,难不住我。我想见见干部再说。当然他们是不会让我见的。
第二天恶人贾寅卫还是照常逼我做三姿,可他们不让闭眼,我脸上爬苍蝇也不让赶,我心一横,不做了。恶人威胁我说,不做再狠整你,你只要写“四书”就不整你。又威胁我说:“不转化,又不做三姿,那就给你吹吹气球(“吹气球”是另一种酷刑,就是用水管插进肛门里灌水)、骑木驴(“骑木驴”就是用木棒往肛门里插,整死你白整死,又没人知道,又验不出来伤)。这会儿,上头叫杀你,我立马杀了你。你刚来又不知道情况,你打听一下,凡是来到郑州监狱的法轮功都‘转化’了,只要你坚持,有你受的罪,先整你三月,再调换监区整你,看你转化不转化。”
另一恶人安松昌说:“××监区有一个犯人不想干活,把自己的胳膊弄骨折了,我们就给他弄到医院去治,你知道吗?那医院的医生都是犯人当的,是我们的铁哥们,只要我们说一声,他们给他接骨接上后再给他折断,反复折磨他,让他生不如死。”
无论他们怎样威胁我,我就不做三姿,他们只好暂时把我严管起来,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于是我就趁恶人睡觉之机,主动找同修交流,三个同修告诉我,这里的确很邪恶,如果不“转化”,恶人们真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你。
有个同修叫宋旭,绝食一年多了,瘦的只剩四、五十斤了。有个同修叫鲁顺民,不“转化”,已经被迫害两三年了。十二监区的老一把手和一个干事用电棍电他口腔,硬是电了一晌。恶人们还用杠子压他的腿,用打火机烧焦了他的手指,连续十五天不让他睡觉,闭眼就打。再后来又调换了六个监区折磨他。同修孙豪杰做“三姿”,被蹲的两腿肿粗多天。同修吴朝刚不“转化”,恶人们用木棍往他肛门里插。
刚开始,我一人炼功,他们也没有管,后来十多位同修都炼,狱警和坏人们害怕极了,他们就将大法弟子王凯坡、陈云龙、姚恒社和我等单独分开严管,每个同修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骂和折磨。
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五点半左右,五监区的两个严管我的恶人叫我看电视暴力录像片。我不看,他们就找来坏人组织的头儿叫陈占洲的恶人逼我看,我说:“按规定六点半是看新闻的时间,现在是属于我的自由时间,我不想看那暴力录像。”陈二话不说,上来一手抓住我咽喉,把我脖子掐出了血,另一只手握拳朝我胸部狠打。这时我高喊:“陈占洲打人了!”后来又来两名恶人准备打我,我又高声说:“你们要再打我,我就撞墙”。陈站州手指住我恶狠狠的说:“你给我撞!你怎么不撞啊!”(我们师父要求,修炼人不允许自杀。)但我已承受不住恶人的折磨,话已出口,大法弟子说出的话必须得算数,也为了不再让恶人迫害其他同修,我就决定真的跑出飞快的速度将头部撞到了监舍的砖墙上。当时“咚”的一声,冲击力把我一颗门牙也震破掉下一半。但是头部一点伤也没有,也不疼。
三天后,我在夜间悄悄的写了申诉书,(因为白天在监视无法写)我把申诉书投进了狱内设的信箱里,另备一份找到五监区的狱警,控告他们指使坏人打我,他们严重的违反了司法部的《六条禁令》,五监区的狱警郭建敏说:“你也别告了,你们是做好人的,和一个没有素质的人犯人计较个啥。你炼功传抄经文是违反纪律的,我们就没追究,咱们摆平算了。”我接着给他讲了真相:“你们也知道我们是好人,根本无罪,你对大法弟子好,我们也都记着,但你们如果还要继续迫害我们,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就给你们上网曝光,我把你们告上法庭,追究法律责任。”狱警接着说:“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是法院判你们的,与我们不相干。”于是他就把打我的恶人骂了一顿,又让其给我道了歉。我告诉它:“只要你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别再迫害大法弟子,就原谅你们。”
零六年七月,迫害我的五监区干部找到我说:“我们想让你早点回到家里去,给你少报几个月的刑期,但你得写个对法轮功的认识。”我说行,于是我就写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弘传全世界,大法弟子无罪,把迫害大法的元凶江泽民推上人民法庭的审判台。其他犯人说:“你真傻,给你减刑你们都不要,我们想都想不来。”十月份,干部又找我谈话,说只要写“四书”给你减七个月的刑期,正好回家过年。我说我不写“四书”,什么减刑不减刑的,压根就不应该关我,我无罪。于是我写了一篇真相资料交给了狱警。
零六年十一月,五监区突然领导大换班,监区长和四个主要的狱警干部全部调换。新上任的狱警监区长刘万超逼我干活,我不干,我说我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我是受迫害的,我无罪,你没来时,他们差一点把我迫害死了,还让我干活,我不干。结果他只好说:“你只要到工地就行,到那你看哪舒服,你就坐哪歇着。”我不参加点名,刘万超就叫恶人打我,把我抬到大厅点名,我就不答应。总之一切不配合,后来也就不管我了。
强加给我的刑期只剩十天的时候,狱警把我抽调到九监区强行洗脑。犹大张少锋、田玉玺强行给我灌输邪悟的东西我不接受,他们逼我写“四书”,我不写,他们就发脾气,还骂我。
九监区的狱警怕我影响他们区的“转化”,我还剩五天就要出狱了,他们又把我调回五监区。零七年十月五日是我闯出监狱的日子,狱警不让通知家属来接我。早晨不到五点,我原籍镇政府的三个干部和一名派出所长开车来把我拉回去后,就把我软禁起来,原因是中央的十七召开,怕我上访,派几个乡干部陪着我,限制我的自由。我强烈抗议,要求见有关领导,他们说这是上级的规定,等十七大会开完了你想去哪就去哪。十月二十二下午,十七大会一结束,他们才把我放了。
由于镇政府将我开除了公职,从2000年以后全部停发了我的工资。我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2007年12月我只好又去了北京原来的单位打工。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5/9/17/1525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