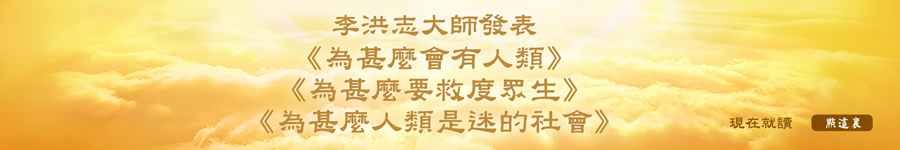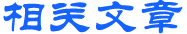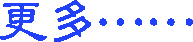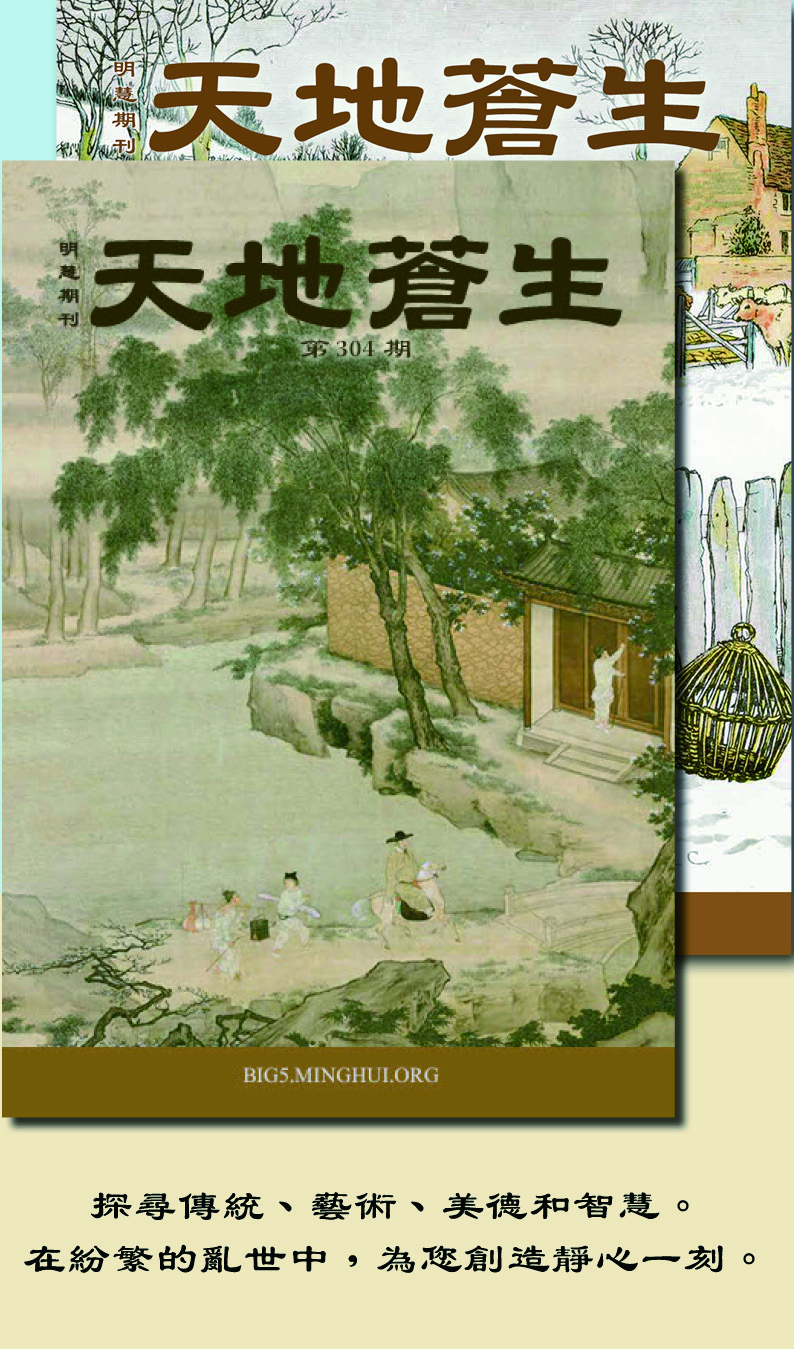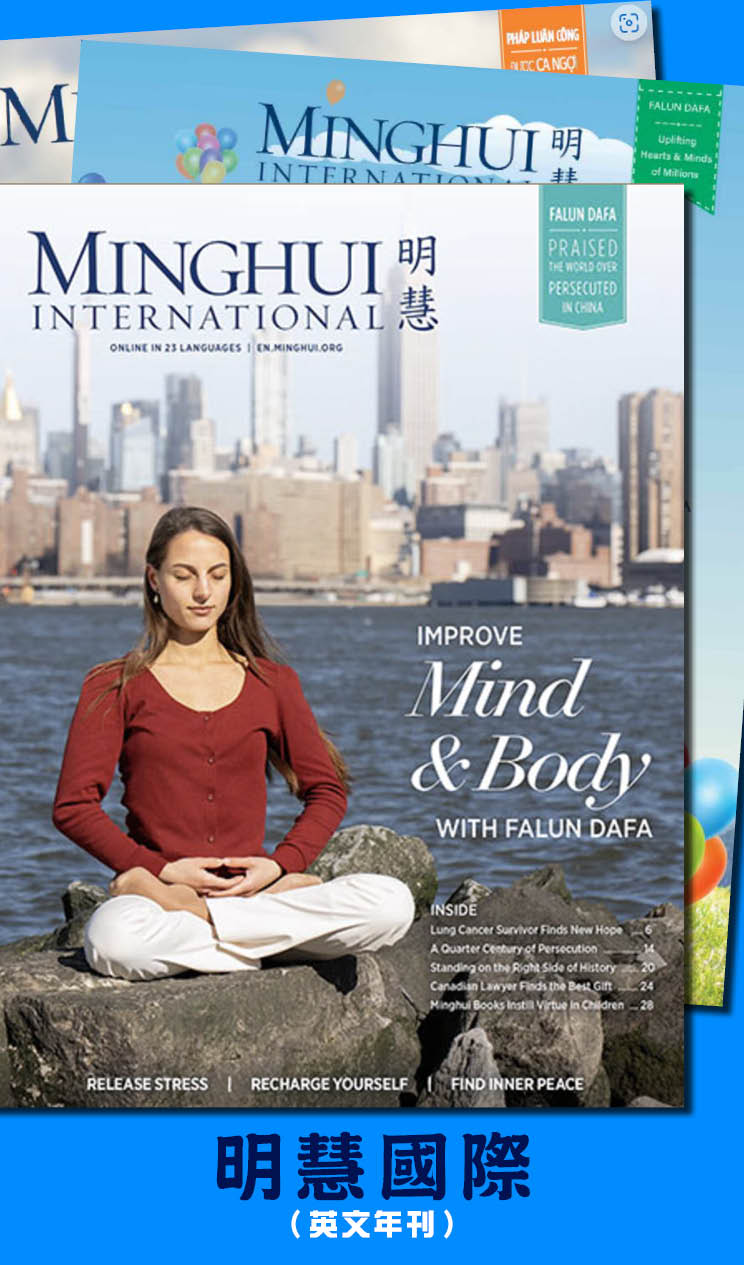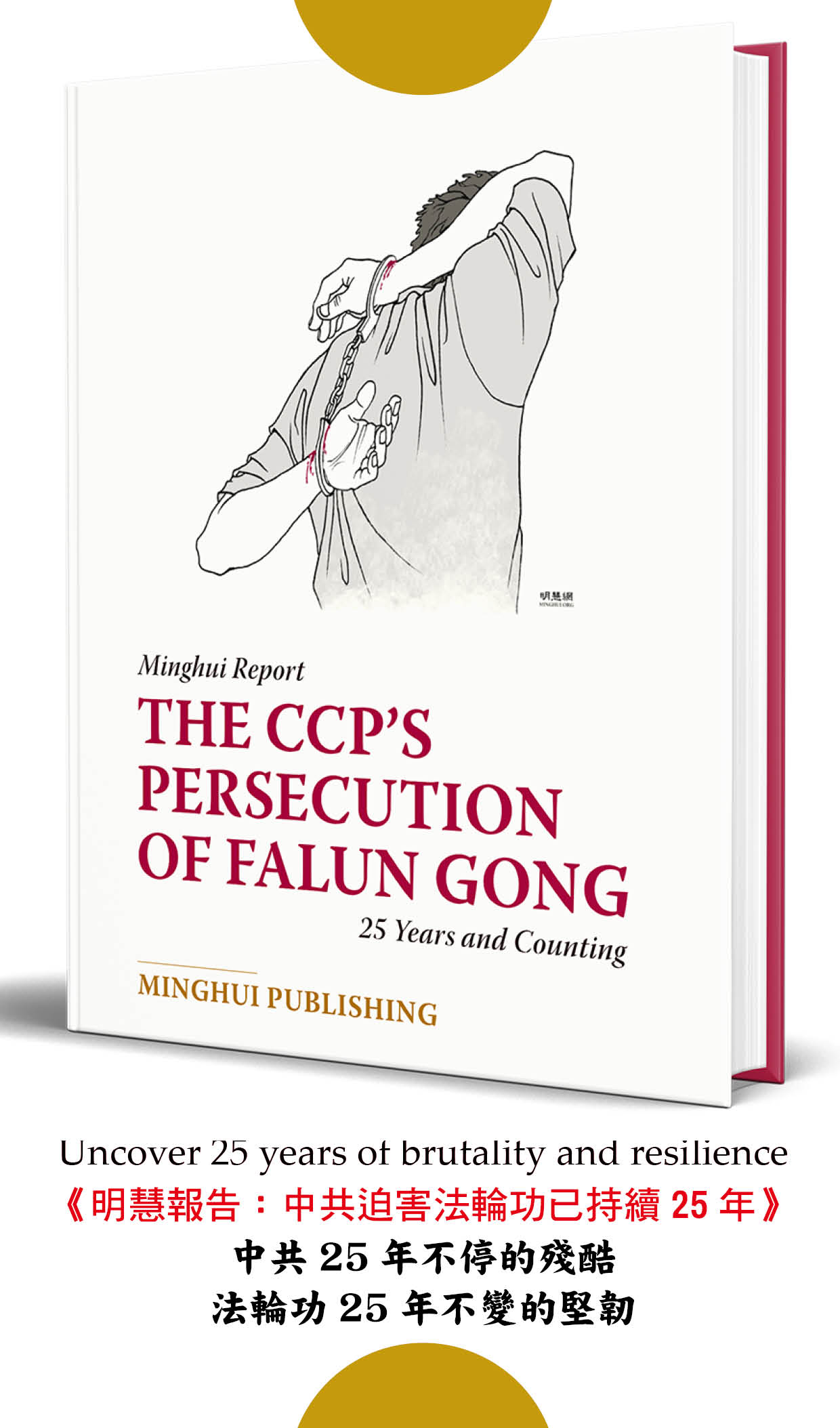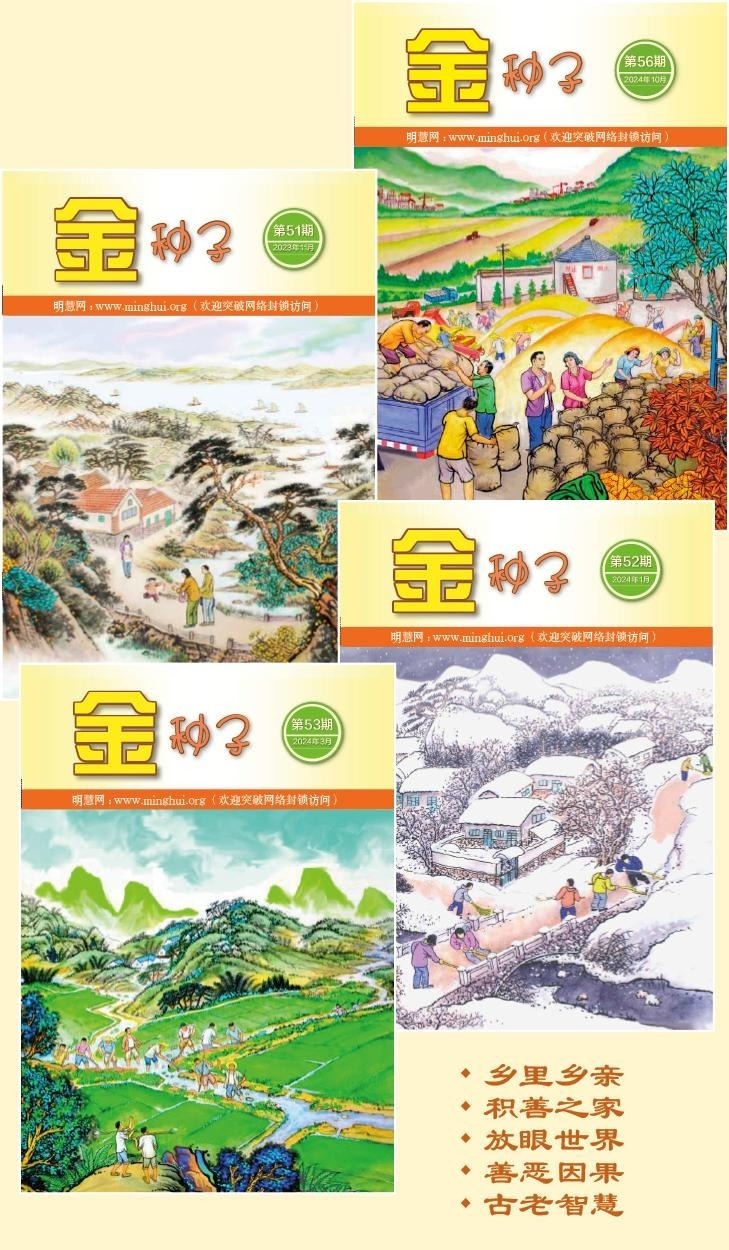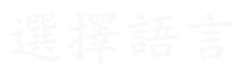遭迫害几乎无法生存 黄凌燕控告元凶江泽民
黄凌燕女士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以下是黄凌燕叙述遭迫害事实:
我叫黄凌燕(小名黄兴娇),初中文化,一九七四年出生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横江村三泽里自然村。因父辈遭遇历次运动才搬家到山凹里。这里只有十多户人家,上学要走山路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度过了童年。
患绝症,幸遇法轮大法
大概九十年代初,二十多岁左右的我经常胃痛,脸色苍白,严重时满床打滚。有时流血难止,经血都要用盆接,有时在路上走着走着,一阵难受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都不知道啥时躺在地上的。后来我偷偷去县城医院问医生,说是一种血液病,类似白血病吧,要求我通知家里住院检查,看着因贫穷而啼哭的父母,我暗下决心,死也不连累父母。此后我只身随缘到了广东佛山打工,有时身体太痛苦了,就幻想着哪种死法即不难看又不连累别人。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早晨我想去垂虹公园呼吸新鲜空气,无意中看到很多人在打坐,有老年的、中年的、年轻的,也有小孩,给我的感觉太震撼了。一问是佛家法轮功,还免费教功。经介绍我在佛山图书馆买到《法轮功》和《转法轮》,从此走上法轮佛法的修炼,按真、善、忍理念做人、做事。一个月左右,我就体会到脱胎换骨的变化,无病一身轻,那种喜悦、那种幸福无法用语言来感激师父,感激大法。
三个月后我回趟老家,父母因信仰基督教而排佛,但看到我气色变好也不反对我教黄振宇、黄振宙两个弟弟炼功(小弟黄振宙从小听力、语言不正常,有残疾证,没实质读过书)。两个弟弟后来都到佛山修炼大法,受益很大。没读过书的黄振宙还在几千人的会场做过心得体会报告,这种超常无法想象。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我和同样修炼法轮功的乔军华在佛山登记结婚,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顺产一个可爱的女儿乔丹凤。一家人生活温馨、和睦,邻里相处都很好,房东把两小孩都交给我们辅导学业,跟我们学真善忍做好学生。
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与人为善,与世无争,身心都获得了很大的益处。
一年搬十多次家没人敢收留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晨炼被人无故骚扰,七月二十三日,乔军华在电视塔公园晨炼被抓,随即被非法抄家,录音机、录像带、大法书籍被抢走,被并逼迫放弃信仰。下午放回后,监视住所、跟踪,环境感到恐怖恶劣,已没有我们说真话的地方了。黄振宙帮我照顾刚满周岁的女儿,我和乔军华在功友的资助下当晚坐飞机依法进京上访。
此时的北京到处便衣恶警,到处设岗盘查,我们在上访没达到目的,几天后就没费用吃住了,流浪了二十七天,于八月二十日早上六点被绑架到西单公安局。经历了残酷的审问后,我和很多法轮功的功友一上来先被暴打一顿,警察打我们像打沙包一样,一轮下来个个都挂彩了。半夜把我们关进一所大监狱;第二天我们被迫做手工加工鱼饲料,八月二十三日,我们被佛山“610”派人押回佛山。身上的钱和银行卡里的工资被强行取走,共二千八百元。
因坚持修炼,乔军华被迫下岗,我又因带小孩没工作,全家身份证被扣,又无法找工作,没了生活来源。“610”派人跟踪、监视我们,经常借口查出租屋,我们因身份证被扣,不给办暂住证,他们随时抄家,随手抢东西,随便抓人。有次警察抓走乔军华和黄振宙,关进石湾看守所,留我在家看孩子,还勒索我要活动费,当时家里只有一百多元钱,我让乔军华带上一百元,结果一到看守所就被抢走了。黄振宙被关了两天被罚交二百元才放人。刚回来房东受不了株连、骚扰,又要我们搬走。我们因此在一个月内搬了六次家。无法安定。我们一家无奈求房东帮我们保管家具,物品,借些钱二次进京讨公道。后来借钱给我们的贾书萍因此被劳教一年。
因身份证被扣,盘查更严厉,我们只能带着小孩和黄振宙在郊区流亡了几天,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半夜在复兴路的一个小公园里休息,被大批武警包围,我和黄振宙被绑架到月坛派出所,乔军华带小孩被冲散,(后也被抓送回佛山拘留十五天,小孩被送亲戚打工处)当时送往月坛派出所有二十多人,有老有少,二十四小时不给吃喝,也不给外买,只要说话就“开飞机”体罚。然后黄振宙被福建驻京办领走,我被关到收容所一天,强迫在地面温度五十六度的广场暴晒。第二天也被押到驻京办。在杂物房里和小弟一起关了五天,两张破沙发,脏乱的被子,每人每天要五十元住宿费,饭钱另计。后来霞浦“610”派了两个人,一个是民政局的吴振顺,一个是公安局的阮志兴,把我们押回霞浦,到公安局门口,行李包仅余二百元被吴振顺搜走,我被拘留了十六天,黄振宙因有残疾证关了三天让爸爸交了三千二百元保出,说是路费和吃住费。后来父母总共花了三千六百元他们才放了我,连收据都不给。
 中共体罚演示:开飞机 |
黄振宙回到佛山后,保险公司说公安局来人给压力,不能让他在那上班洗车了。后经同事介绍去环卫公司当清洁工,被安排在彩管厂搞卫生,乔军华也回去原单位彩管厂做保安,我在天马饮食公司当前台接待。
一年来,佛山国安排人经常造谣、恐吓房东,强迫我们搬了十多次家,有一次在下暴雨,他们不让我们租住在他们管辖区内,就动手把物品扔出去,还没找到下家房子,只好请了一辆货车,他们特地看着我们一件件搬完,开着车去再去找房子。那种凄惨、屈辱,给小孩造成的惊吓,至今无法抚平心灵的创伤。
警察要赶尽杀绝第三次进京鸣冤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振宙在街上发真相资料,因不配合警察搜身,当场被捆绑起来暴打,全身受伤,反被诬告袭警抓去刑事拘留。到了拘留所就被脱光衣服搜身,然后只穿一件裤头关进监仓,警察还指使其他犯人对他拳打脚踢。逼他做手工——叠花,不做就不给吃饭。一个星期后,“610”人员把他吊铐在车里押送到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在劳教所被强行剃光头、吊铐、关禁闭、包夹、不给睡觉、长期劳工,吃用要自己付钱。二十九日下午,我在公司开会,两便衣送来黄振宙体检收费单,要我付六十五点八元,上面注射费四元八角,我问他没有病,为什么要打针?打了什么针?他们不说,我没带那么多钱,就叫我去同事那借,付了款就走了,我和黄振宇几次到公安局探问都不给见面。当晚又来我住处抄家,拿走很多真相资料,四面装裱好的挂像,四套秋冬运动服(白色)一件夏天短袖衫炼功服,炼功照片和简介挂布等。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一片狼藉,无从下脚。当晚把我从单位放回看小孩,乔军华又被刑事拘留了,后来要他保证脱离法轮功才放人。
我们没有配合,乔军华被送去三水劳教所“洗脑”。我去政保科找领导要人。他拒绝接见,叫个曾参与抄家的警察带话:刑事拘留不同于治安拘留,没把问题交代清楚,不从思想上、行为上完全“转化”是不可能放人的。我说:你们政府怎么能这样迫害我们,一年来逼迫我们,驱赶我们十多次,几度造成我们生活危机,我们都无怨无恨,处处要求自己做得更好。如今小孩受惊吓天天哭闹要爸爸,扁桃体肿大,整个下巴都变形了,幼儿园老师怕传染给小朋友,要我自己带小孩,这样我也上不了班,你们这不是把我逼上绝路吗?警察说:不是逼上绝路,是要赶尽杀绝。
我无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带小孩第三次去北京上访。十二月的北京已经严寒,冷入骨髓,没有暖气,没有热水,我和小孩第二天裸露出的脸和手都爆裂了,好不容易到了天安门广场,就被围过来几个人推扯上警车,说我不像旅游的,就是法轮功,小孩被重摔倒在车上,然后打我,牙齿被打松一个(回到广东就掉了),很快就抓满一车人开进广场公安局,简单审讯后,大家都不报姓名地址,就一个一个被押上一辆大巴车,那时对每个人造成的心理压力,恐惧无以复加,随时都面临集中营,酷刑,折磨与死亡。我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把车窗都关上,窗帘拉上不让外面民众听到。
当开到郊外时突然停车,有人过来叫我快点下车,说一看就知道你是南方来的,看小孩遭的罪,尿湿的裤子都结冰了,回南方去,不要再来了。我说法轮功修真善忍,我们都没犯罪,要求全部放人。后来听说这一车人在路上都被放了。广场的便衣看到我又带小孩回到广场也不抓我了,都说没人敢处理我的诉求,除非把江泽民抓了、判了,回去等机会不要再来了。
我又失望的回到寄放行李处,碰到山东济南一同修,被电击,酷刑折磨了一个星期,放出来时体无完肤;衣服扣子拉链都被剪掉,皮带也被拿走,没穿鞋光着脚在寒风里走到我面前。他说当时炼功才四个月,全家受益很大,是和妻子一同上访被分开迫害,后来我包里的钱刚好可以买两张车票和路上吃的面包水之类的,回到广州兜里只有八块钱了。无家可归,不知何去何从,后来碰到汕头的大法弟子,就跟他们一同在广州流亡,乔军华从拘留所出来也无家可归。
被非法劳教时奶奶悲愤离世
一家人带着小孩在外流离失所,没有工作收入,大家互相接济,物质需要已减到最低限,但也维持不了多久。
我于二零零一年五月二日又被绑架到广州白云区公安局,警察把我们母女俩关进一个铁笼子,当天打雷暴雨,我和小孩又冷又湿,一个好心人拿张报纸让我给小孩挡风。我抗议这种非人的待遇,不配合任何的审问,二十四小时后还没找出我任何犯罪的证据,就把我们母女送到附近所有关押犯人的地方,都因我带着小孩又没有犯罪证据,不收监,最后折腾到半夜把我们关进广州白云戒毒所,强制“转化”、包夹、体罚、不给睡觉,我绝食抗议两个星期,被几个高大的保安按住强行灌食、打针、最后食管从喉咙顺着嘴出来,没灌成,却造成我大口吐血。后来他们不干涉我炼功,其实他们都知道炼功是对身体最好恢复,每当有记者采访或有领导视察,就把我们母女俩和一个快临产的湖南籍孕妇关进储藏室,等来采访的人走了以后才能出来。
六月二日,我被霞浦“610”派人接回父母家,禁闭在家里,临走前我要求回出租屋拿些换洗衣物,还有借来的二千元钱。他们都不许,说抄家时早被搜走了,在家里我穿妈妈的衣服。他们派人二十四小时看住我家四个门,每天都找来一些学者专家来家里“转化”我,有个干部竟然说学什么不好非要学法轮功“真善忍”跟政府顶,你看村里谁谁黑白通吃挣了多少钱,你看村里谁谁杀了人,花几十万就摆平了,哪像你们学“真善忍”还要坐牢,这里进、那里出的。
父母被叫到村大队强迫在保证书上面画押按手印,如果我还上北京就抓我父母坐牢。天气越来越热,农村蚊子多,那些看守监视的人吃不消;在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我女儿过三岁生日这天,县里来了六、七辆车,说是接我去县里买几件衣服,有省市的领导来看我了,穿我妈的衣服不好看,我不相信他们,他们说让我妈和小孩都去,不会骗我的。到了县城让我妈带小孩在公安局坐会儿,说宁德地区领导指名要见我,就一会儿,小孩不愿与我分开都哭晕了。我被带到龙首山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头有几个领导模样的人坐着,我也不知道是那个部门的谁,他们把工作证有相片和名字那面往里翻,就开始逼我放弃修炼,保证不炼功、不上访,给我最后机会,否则连累他们不会给我好过的。我跟他们讲我炼功只图有个好身体,按真善忍做更好的人,怎么就连累你们——我甚至谁都不认识的人,这又是啥道理?
他们看我不配合,命令马上把我背铐起来送走,拖上车直接送往福州市山区建新镇台屿村(省女子劳教所)当时霞浦到福州段在修公路,那路非常颠簸,我被连司机共七人在中间;后排的人用手拉起让我处于反吊状态,加上公路坑洼,使我的头不断撞在挂挡后面那个突起的地方。大概六、七个小时后,我的额头破了,脚肿得不能走动,手铐嵌入肉里拉伤了筋,后来一个月动不了。眼睛连哭带撞到肿到了睁不开、看不见的地步,就这样被几个人从只有车辆进出的门抬进了劳教所,就这样不用任何手续,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绑架到劳教所一年六个月。一进劳教所我就被强制剪发、包夹,二十四小时不给睡觉,体罚,关禁闭,轮番洗脑轰炸,逼看造假诬蔑法轮功的东西,强迫“转化”,强迫生产劳动,没完成就加班到半夜。
妈妈等不到我,就知道被骗,就在公安局哭闹,被送回家后就精神不正常了,经常不穿衣服就跑街上骂共产党、骂村干部。
奶奶年岁大,受不了孙辈们因为修真善忍做好人,被害的一个个都见不到,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悲愤离世。奶奶在世最疼我,去世时我都没机会送终,这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我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出过县城,也没人知道我被关哪,爸爸上有老下有小还要照顾疯癫的妈妈和我的小孩,丈夫、弟弟都被非法关押,所以在我被关押期间,无人送衣物,没有亲人探视过,期满还拖了三天说我情况特殊不让自己走,等“610”来接。我回家后,看到奶奶没了,女儿都该上幼儿园了,妈妈病重又检查出肝腹水,看着苍老无奈的父亲,我跑到屋后山上大哭一场,感叹这世道想做好人却如此艰难。
我在家休息了几天,又带着小孩回到佛山打工,最早在她那儿住过几年的房东潘姨看到我,同情我们无辜遭迫害,主动把房租减半给我们住。慢慢又安定下来了,女儿也上幼儿园了。
大弟遭酷刑家庭离散
大弟黄振宇目睹七二零后法轮功遭遇太多的不公,亲人遭遇太多非法关押,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依法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五个人扑倒,一个踩头,二个按住手脚,二个踢打全身,他当场被打掉两颗牙齿,强行拖上警车开到公安局。因不报姓名地址,被推进一间屋里,拉上窗帘,用三节棍和胶棒打,打完再戴上手铐审问,然后随便定了罪名把他关进看守所。因不报姓名地址,又拿电棍电后背和下体敏感部位。然后又被押往另一个看守所,里边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戴铁帽脚镣手铐脖链,手脚铐在一起,不能坐,不能站,不能蹲……
在那里,他们把所有不报姓名地址的法轮功学员集中编号。然后押上大巴车,大概有二十辆左右开往辽宁。黄振宇他们那辆大巴开到辽宁皋新,被关进重刑犯监狱再遭受酷刑迫害。警察指使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折磨他,谁卖力就给谁减刑。二十四小时不给睡觉,不给盖被子。第二天三个人来提审,然后又叫进两个人按住手脚,压在地上用很粗的木棍打,最后木棍打断,他的屁股也被打烂,拉起来眼睛都看不见东西了,一个“610”头子有些害怕出事,就把他弄到椅子上趴了一会,另一个说这小子怎么这么不经打。过了一会又被架回监仓,白天逼做手工针线活,收工后牢头留几枚针,然后拿针扎黄振宇的膝盖,有几下用力大了,针扎进去半天都拔不出来。到了晚上把他衣服扒光衣服,打开窗户然后拿冷水从头往下淋,外面气温大概是零下十几度,大雪过膝,水流到地上马上结冰。每次提审,那些警察都把他当沙包练拳脚一样,还故意用手扭抓受伤的屁股。监仓里牢头为了多减期,经常发动里面十几个人对他拳打脚踢,脸经常被打的肿胀变形,牙齿被打落四个,眼睛也肿的看不见东西。有人来巡查就把他遮挡在后面,他一直绝食抗议,又被插管灌浓盐水。一个月左右把他折磨的严重脱相,人瘦的皮包骨头。南方人冬天在北方零下十几度的地方受酷刑那个惨,无以言表……恶徒们还威胁恐吓,反正早晚要把他弄死,再不说就会被送到某地,死了也白死,都没人知道。
每天这样承受没人性的折磨,夺走了多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的生命。痛苦中黄振宇非常想念亲人,担心母亲的身体承受不了失去儿女的痛苦,无意中就透露了自己是哪里人。过了几天,霞浦“610”派人接回黄振宇,那时的他面目皆非。据柏洋派出所所长说:把人折磨成这样还不能问,当时跑的快,如果不是当天就走恐怕就没命了,谁受得了那样的罪啊。回到霞浦又被关进看守所一个月,准备非法判他两年劳教。后来单位岗位不能缺人才将他保出。
回单位后,“610”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派人去厂里录音谈话,搜查住所,还到其他同事宿舍无证搜查,搞的厂里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厂里领导本来要提他当主管,也推迟了几年,怕他再被迫害,到时很难找人替他岗位。
他的前妻因他炼法轮功被迫害,株连她没有安全感,搞了外遇要离婚,法院判不离。第二次她以黄振宇还炼法轮功无法保证她的幸福为由,法院就给判离了。可怜他的女儿还不到五岁就要承受破碎家庭带来的不幸。
丈夫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在二零零一年过年前夕,乔军华第三次依法去北京上访。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正上演自焚伪案,他还没接近广场就被抓,被暴打,戴手铐、脚镣、铁帽,手脚锁在一起,不能站,不能蹲,不能躺;用电棍电,打烂了新买的羽绒服,牛仔裤断成了一节一节的布条,头上的血染红了贴身的白衬衫,都脱不下来,看着人已经不行了才被拖着扔到火车站。不知过了多久他意识恢复些,就向民众求救,后来在广东的好心人帮助下回到广州。当我们功友把他背回来,内衣内裤都被血粘的很难脱下,脚镣的印痕深深嵌在肉里,腿肿得不能移动,炼功了十几天才慢慢恢复。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日,乔军华去他妹妹处借钱被蹲坑抓捕,株连他妹妹一家也被抓去关里了三天,写了保证才放出来。然后乔军华被押到三水非法劳教二年,经历关小号,包夹,剥夺睡眠,被吊铐,打骂,电击,绝食反抗被插管灌食,强制“转化”。
二零零五年亚运会期间,乔军华因跟厂里工会领导说些共产党尽搞假恶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没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劝领导注重道德修养之类的话,否则再大的工厂早晚也会出问题。就这样他又被厂里管制了,有天上班时突然跑回家说来不及了,有人要害他,找不到地方躲藏,然后浑身冷汗,眼神发直,脸色蜡黄,突然大喊大叫,拿头撞墙;我看着不对劲帮他请了病假,找他同事,说厂里又逼他写检讨,写诽谤法轮功的材料,派人成天跟着,上厕所都跟着,可能压力太大,精神崩溃了。
乔军华离开厂里差不多一个月,就恢复正常,就回去上班了。可是不到两个月,突然有天他厂里通知我去接他。当我下班赶到时,他同事报了警,公安也介入了,我看他穿着工作服站在员工过道,直挺挺的站着,眼睛怒瞪着,推不动,拉不动,他同事说一整天都这样。看到我来,突然直挺挺倒地,眼角流泪,不会动,不会说话。我质疑是不是给他打毒针,吃毒药了。公安局的人回答说:检查过身体没有针孔。我叫他同事帮忙抬回家。厂里没作任何解释,休息两、三天,恢复点精神就被厂里叫去写自愿辞职,半个小时所有手续办完。我去找他领导说理,一个为厂里贡献十多年的员工在厂里被迫害出事,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就这样辞退,连基本人道都没有。还说办完手续了一切跟厂里没有关系,连社保都给他停了。后来这个多少亿资金的,几千个员工的合资大厂养着一大批贪官,几经易手最后完全倒闭。
没了工作,从此真的崩溃不可收拾,房东说吵了其他房客,无奈又要我们搬走。此时我正离家一个小时公交车程的南庄杏头替黄振宇管理车行(保养,三级维修)汽车。我带乔军华到附近租了房,但他没有安全感,老往外跑,有时一跑就是半个月,二十多天,在外面捡垃圾吃,睡野外。后来严重时不让我上班,不让小孩上学,赶工人走,赶客户去别家保养。一个叫陆永锦的客户报警叫了佛山第三医院(精神病医院)救护车强行拉到精神科,陆永锦替我交了五千元押金,一个星期就花完了,医院要我交钱;没了社保我无奈应付不了昂贵的医药费要求出院。当时听说公安已介入找领导谈话,我害怕再遭迫害赶紧办了手续出院,刚到家安顿好,当地派出所就到车行抄家。修车师傅看不过说了句“你们公安怎么老抓好人,不怕遭报应啊”,就被抓进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我带着乔军华又流离失所了,车行无人管理转让给一个客户,后因道路扩建停产导致无法回本。
我把小孩送回霞浦,带着乔军华流亡到徐州、宿州、南阳,后来他高中时的同学把我们接回老家湖北襄樊。在同学的帮助下我开了一间小精品屋卖女生头饰类,在同学照顾下,乔军华慢慢又恢复了精神,还安排他在同学经营的花场干些除草浇水的工作,后因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又回到佛山。乔军华成了盈保公司的职员,负责看车收费,有一千零五十元的工资,两班制。我不是佛山户口只能自负盈亏承包路段。但佛山给他受到精神创伤太多,他怕我炼功,怕我接触其他功友,因害怕被迫害而经常无故打我和小孩,清醒过来又内疚道歉,后来精神又不正常了,不敢上班。后来双方亲友看我实在太辛苦,为了小孩能有正常成长环境,为了不给他造成压力就劝我们离了婚。我独力抚养小孩,有空就带小孩去看看乔军华,帮他收拾家里陪他聊天,从此他也把我当姐妹一样。就是不能提修炼、法轮功的话题,怕有跟踪,监控又株连他,总是警告我共产党的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但又向往真善忍的美好,又害怕再被迫害,总是无法摆正关系;经常自言自语。好好的一个上进青年硬是把他迫害成精神分裂症。
母亲悲愤而亡
父母家长期乡里村委安排盯梢,电话骚扰,所谓的敏感日都要我父母作保证或提供我和弟弟的地址、电话,也派人到黄振宇厂里宿舍搜查过几次。小孩的户口上在我爸名下,从小被歧视,所有的福利待遇都没她的份,水库移民金补贴等,所有人都有,就她没有,读书都是高价,回到户口所在地也要交比别人多的学杂费。妈妈在长期红色恐怖高压,病情加重,不到六十岁就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晚含冤吐血而亡。死前最后一个电话说她很恨共产党把我们家迫害得七零八落,她多想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又交代我可以不用参加她的丧礼,小心“610”趁机来绑架我。
要求追究元凶江泽民罪责
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中,江泽民威逼各级领导执行其邪恶指令,致使从市、区、公安、派出所,社区各级“610”,国保大队相关执法部门都参与了对我及家人不同程度的迫害,但罪魁祸首是江泽民,其实很多人也是承受着高层压力,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目前我代表个人和亲人只控告江泽民,把希望和机会留给可能改过的人。
这场本不该有的浩劫,给我家庭带来的痛苦,经济的巨大损失,身体的痛苦承受,亲人的相互担心,思想承受着巨大的恐惧,被剥夺工作,剥夺生存权,孩子受到歧视使身心受到的摧残至今无法抚平。这一切都源于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邪恶指令。
本人黄凌燕代表全家申请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要求赔偿多年来经济损失,名誉损失,家庭破散的损失,亲人遭受痛苦的精神损失,要求至少赔偿三千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