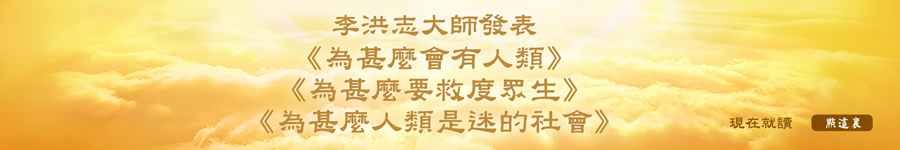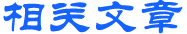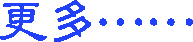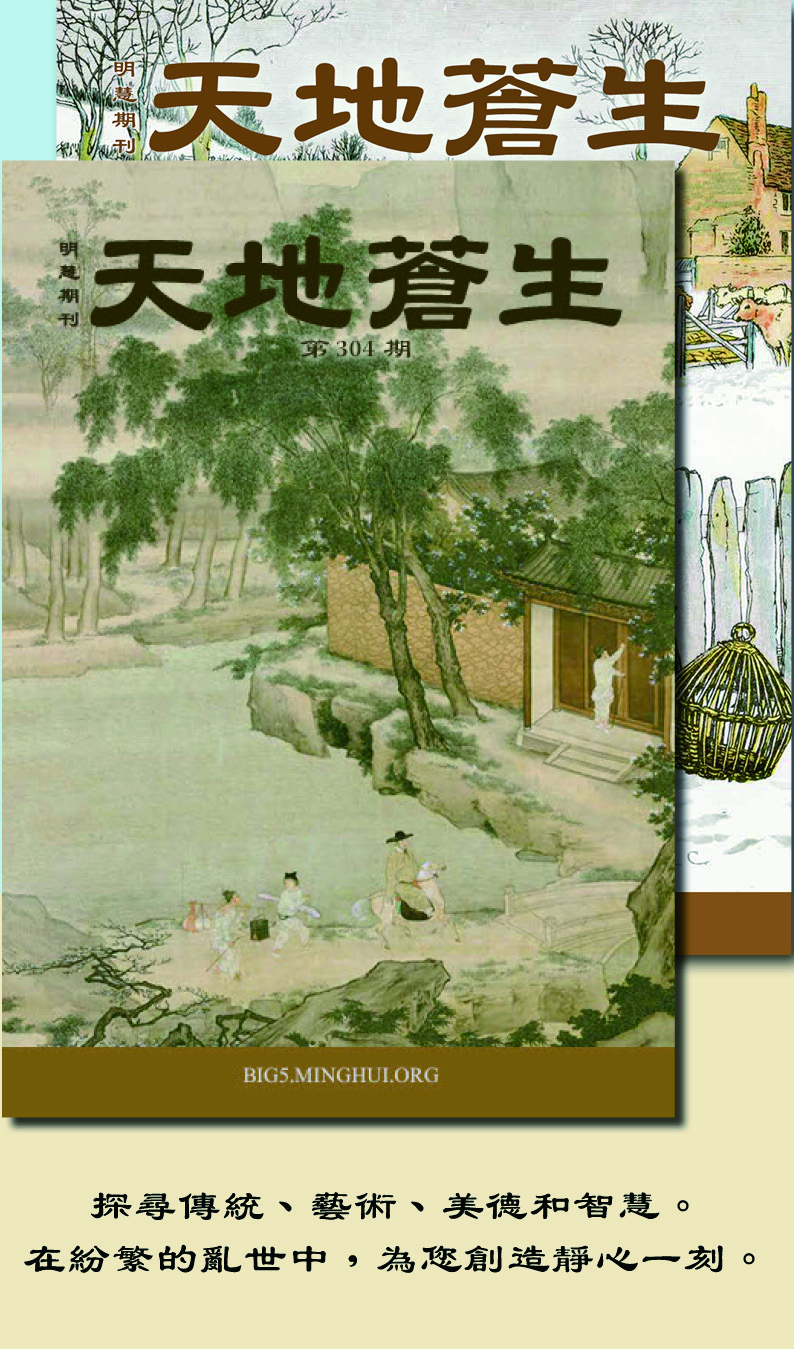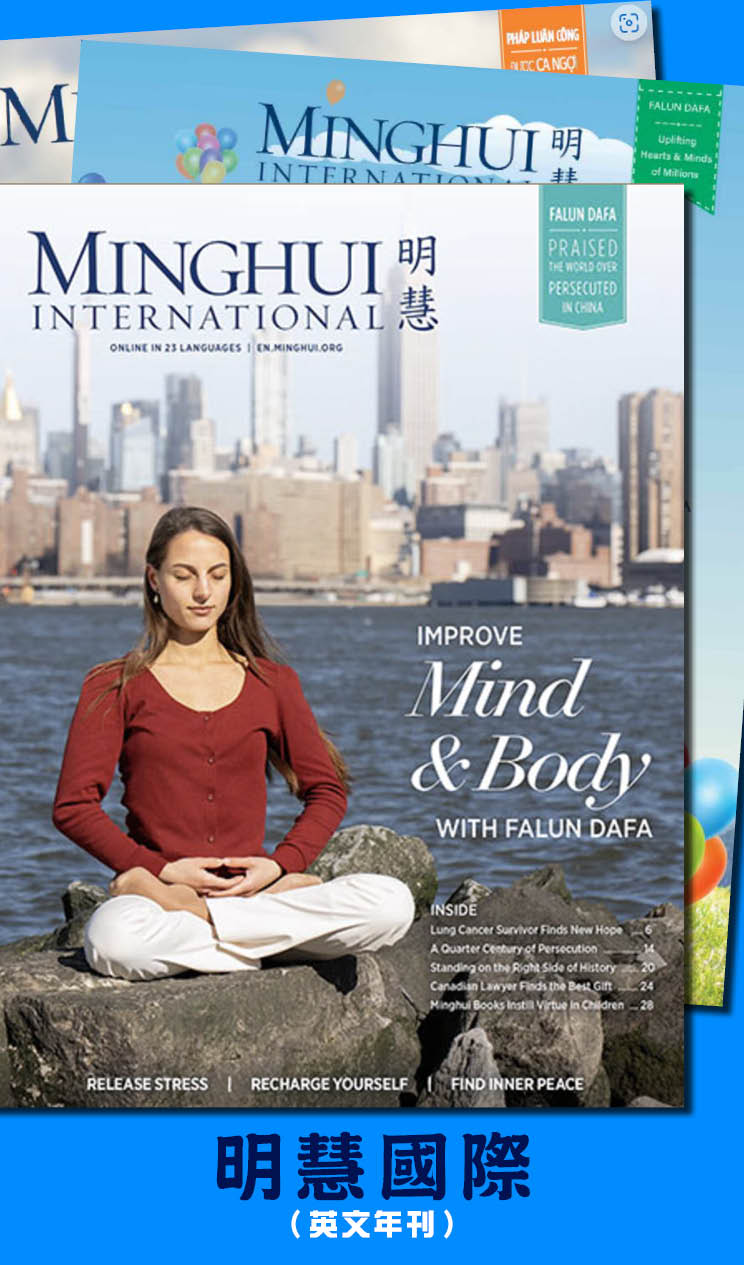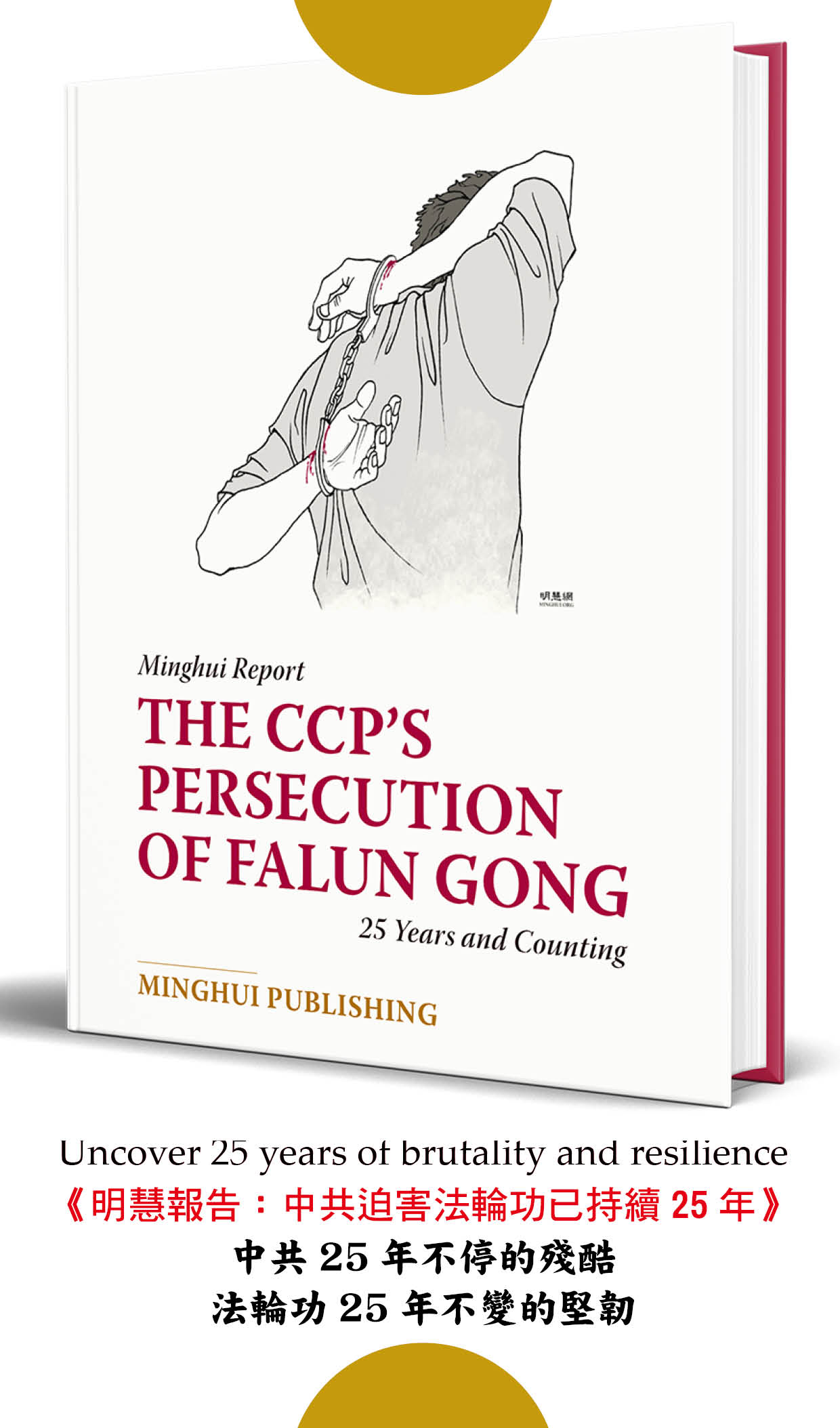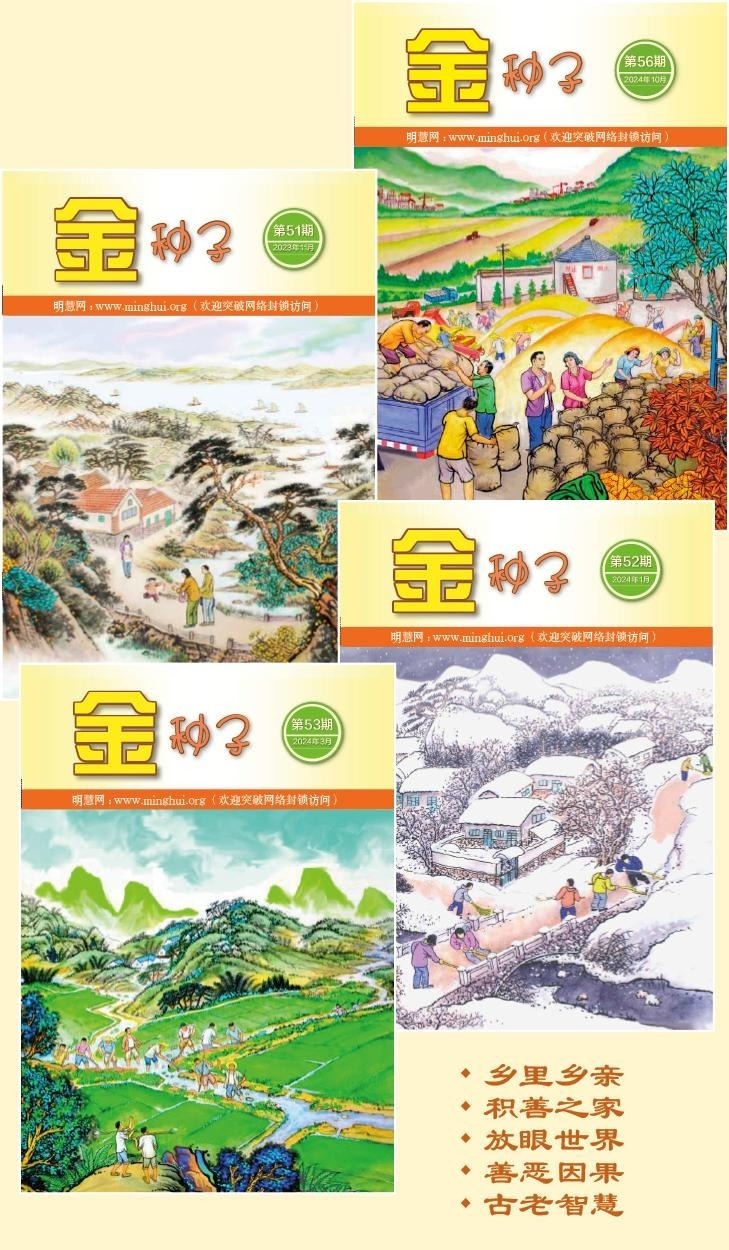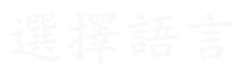中共黑监狱里的几十天
经过半天的审讯,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最后扔出一张纸要我签字,“六一零”头目告诉我这是太原市公安局局长亲自签字要抓我的,我拒绝在上面签字,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好人,他们气急败坏,告诉我签不签字对它们而言无所谓,随后将我戴上手铐,一左一右将我押上警车,也不知道要带我往何处。
我是早上被绑架的,在警车上已是深夜了。汽车穿过整个城市,我被送到一所监狱的门前。一名狱医问我有传染病没有。我说没有,我想我是修炼人,怎么会有病呢。我被开了七十块钱检查身体的收据。就问一句话,他就获得七十块钱的报酬。我的皮鞋被脱下,皮带也没有,光着脚穿过不知多少道黑森森的铁门。
最后我被推进一个像猪舍的地方,昏暗的灯光下,挤满了犯人,有几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露在外面,死刑犯就会被戴上脚镣和手铐的。两个人横躺在炕上,占据炕上几乎一半的地方,其余炕上的人几乎背贴着背塞在一起,水泥地上也是人;厕所门前也躺了一个,看起来面黄肌瘦,原来他患有肺结核传染病,牢头怕传染就让他单独睡在厕所的门前。我的手铐已被解开,我只穿了一件西服,没有被子,我只好穿着衣服,被挤了进去。
我几乎无法入睡,心里想着其他同修的安危、自己的执着……。半夜有两个人搜我的衣服,其实我的衣服里啥也没有,白天已被洗劫过一次了,就一卷纸还在口袋里,但是这点东西也被搜刮了去,他俩说任何东西是要“交公”,其实就是叫给牢头掌管。后来才知道他们俩是专给牢头捶背、端茶送水,伺候牢头的。
早上广播恶声地喊到“起来,起来”,所有的犯人一骨碌爬了起来叠被子,我稍微慢了一点,一个胖牢头(二牢头)就一脚踢过来,我被踢翻了身,竟然平稳地站在地上了,连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随后那个瘦牢头(牢头老大)恶狠狠命令大家喊报告,清点人数。
吃早餐了,有一个犯人替牢头管物资,也是牢头信任的一个当地人。他就给我一个破烂不堪的一次性塑料饭勺子,手柄破裂不堪,也只剩下半截了。我被指令与一个姓张的犯人共用一个塑料碗,那个塑料碗里面黑乎乎的,也不知道是哪个死刑犯留下来的。所谓的早餐就是稀饭,我已一整天没吃饭了。我从一个被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一个修炼大法而心地善良的白领,转眼间被邪党迫害沦为阶下囚,连起码做人的尊严也不能有了。我实在太饿了,也只好勉强吃了两口。那个管物资的犯人将午餐肉,还有一些方便面之类的,首先分给两个牢头,牢头说够了不要之后,其次分给伺候牢头的人,然后就是向监狱里面交了伙食费的犯人。没给监狱交钱的人也就没份了。
原来所有被关押的人家属交的钱都被那个瘦一点的牢头掌管,他们坐牢也不忘买烟和酒等来享受,晚上打牌累了还可以吃夜宵,还买些护肤品之类,买牛奶倒在开水里面蒸脸。监狱里面的费用比外面东西贵多了。犯人家属交的钱就这样被监狱和牢头霸占。瘦一点的牢头也是打架最凶的一个,所以叫老大,他已犯了死罪,因为有关系就呆在监狱里好几年了。我给他讲我被迫害的真相,他说出去也来学,但是一天他们在打牌时,看见我盘腿坐在炕上,他一脚踢了过来,以后就不准许我盘腿坐在炕上。我只好在晚上犯人都睡熟的时候坐在厕所一旁的地上炼功。身旁是那个患有肺结核的犯人。
狱警拿来一床被子,外面是新的,棉絮的中间破了个很大的洞,周围也有很多小洞,即使是这样他们还要收费三百五十块(其实连三十块钱都不值,我出狱时被强迫交纳)。有时我就用这破被子大冬天里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有时还要避让给牢头端尿盆的人。
牢房的另一端有个窗户,窗户和炕之间是个墙,墙上挂了个小电视,每天都是播的警方的新闻。那个窗户下面唯一有阳光可以透进来的地方也是牢头们的私有领地。我的衣服也没有办法洗,洗了也没有地方晾晒,有时我就将袜子在厕所的水龙头下冲一下,就缠在水管上面,因天气干燥,过一段时间就干了。那个会透一点阳光的地方,我去过一次。那是一天中午,瘦牢头要求大家蹲在窗户下,手抱着头,原来武警持冲锋枪进来搜查监狱违禁的东西。其牢头的烟酒等违禁的东西就没有被搜查,中共邪党只是拿枪吓唬吓唬而已。
被关押的几十天里,有一天我被要求走出牢房去照相,我来到太原的时候,那时还是春天,没想到现在已经是寒冬了。外面下雪了,不禁黯然神伤。我与大法有缘,冥冥之中有天意,
我追随师父的脚印走过每一个地方,就在当年的四月二十三日,我从太原出发,一路上还是艳阳高照,我外面只穿了一套西装,途经过雁门关时,天空突然纷纷扬扬下起大雪,漫山遍野,白茫茫的一片。不得就近找个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当离开雁门关后大雪又停了下来,到朔州早已是晴空万里,不见一点下雪的痕迹。
但是这邪党的牢房怎能关住大法弟子的心。邪恶的六一零要我写所谓的“坦白”,我就他们给我的笔写了一首诗
狱中吟
大雪纷飞云惨淡,
盖尽人间路万千。
越岭群燕识归途,
羁身法徒归路艰。
人间岁月似水流,
富贵荣华如烟散。
破壁乘车飞天去,
不负今生随师缘。
没有牙膏刷牙,也没有毛巾洗脸,白天还要坐在炕上干监狱里指派的手工活。说是赚钱给犯人们改善伙食,其实有时早上连粥也没有吃的,就一碗烂菜叶子煮的菜叶汤,喝完汤之后里面剩下的全是沙子。我给里面的犯人们讲真相,后来又进来一个犯人(牢头老三)当时就骂共产党快完了,连炼个功也要被抓。一个给牢头捶背的犯人,一天要出庭,他要穿我的西服去上法庭,我当时想我是修炼的人,修炼人是修善的,给他讲真相后,他也没有为难过我,我就将衣服脱下给他穿上。下午他从法庭上回监狱里来,很兴奋地将衣服还给我,原来他当庭无罪释放了!
一天牢房里面的一个人要被送去枪毙。晚上所有的人都不能睡,都得看着他,晚上他用牢头抽烟剩下的箔纸给他自己折“金币”,叠放在衣物里。我心中很悲凉,感到常人生死的无奈。第二天,他被送出去打针,我看见他用手按住打针的伤口,他即将上刑场,身体不断发抖。
整个牢房里一片悲凉,看来不止一个犯人被拉出去了,牢头要大家唱歌,所有的牢房都唱高兴的歌曲,几个生命即将终结,邪党却要大家唱喜庆的歌曲来为邪党助兴。有的犯人呼叫道别。虽然被迫唱歌,常人的歌声中透着凄凉,生死难卜。人生呀,作恶做善的结局是如此的不同。
我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犯人,我为了反抗邪党无理关押,我就绝食,有好心的犯人拿水给我喝,那个牢头老大要我洗每个人吃饭的碗。一天,他逼迫一个管物品的犯人拿碗粥强迫我吃,我说不吃,这个犯人就脱下鞋子,示意打我的脸,我不想因为我而使他受到牢头的打骂,我就接过那粥,顺手倒掉。从此,没有人强迫我吃饭了。这个犯人有次跟牢头老大打牌,因牢头老大不讲理,他顶了几句,从此他便失去牢头的信任。没绝食的时候,有几次他偷偷地塞给我碗里很多午餐肉。其实我不喜欢吃肉的,只是大法弟子的善良感动了他。绝食之后,头几天特别难受,我后来想到同修做的饭,我就从另外的空间拿过来吃,就行了,身体也就不难受了,而且总觉得肚子是饱的,监狱里的犯人都很惊奇,他们都叫我“法轮功”。晚上我炼功时,也有几个犯人给我放哨。
过年的前夕,我被释放了。走出牢房时,我对监狱里的负责人说,我说出去还要炼,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除夕,到处都是鞭炮的喜庆气氛,我回到家乡。家乡的同修将真相从城市沿途几十公里一直贴到我的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