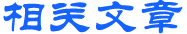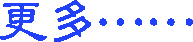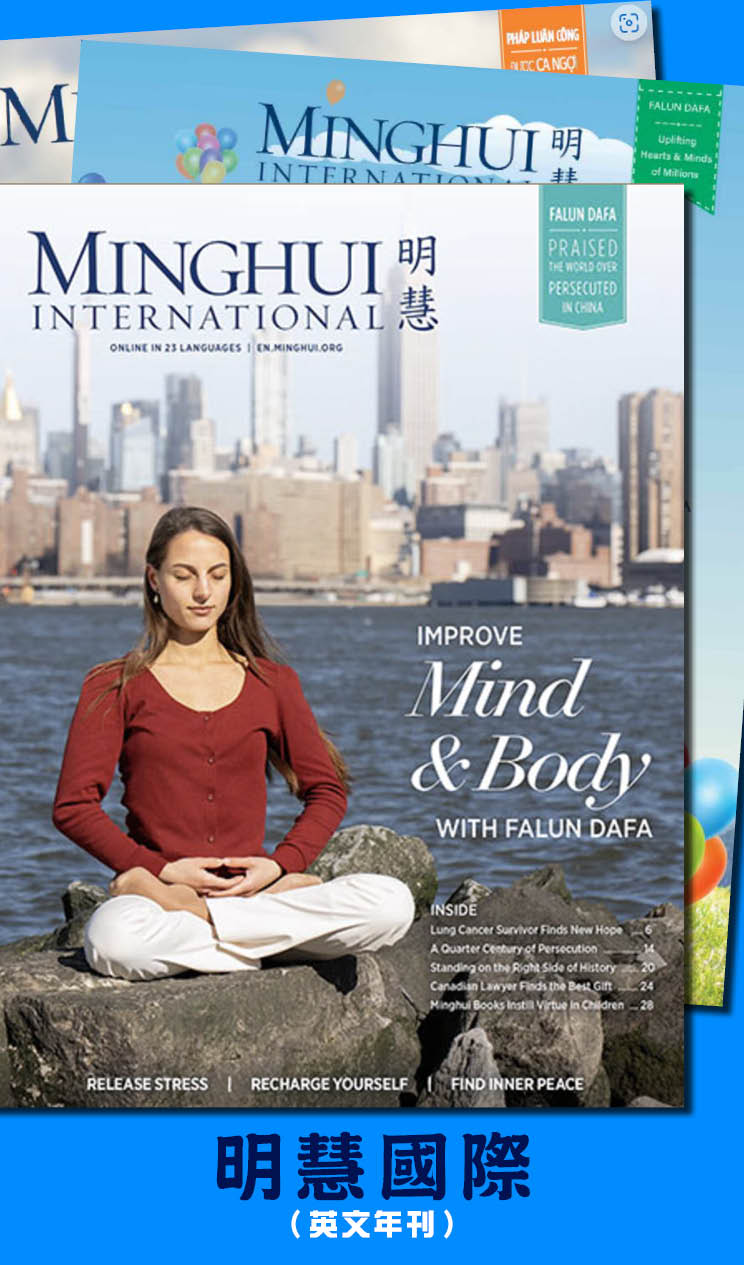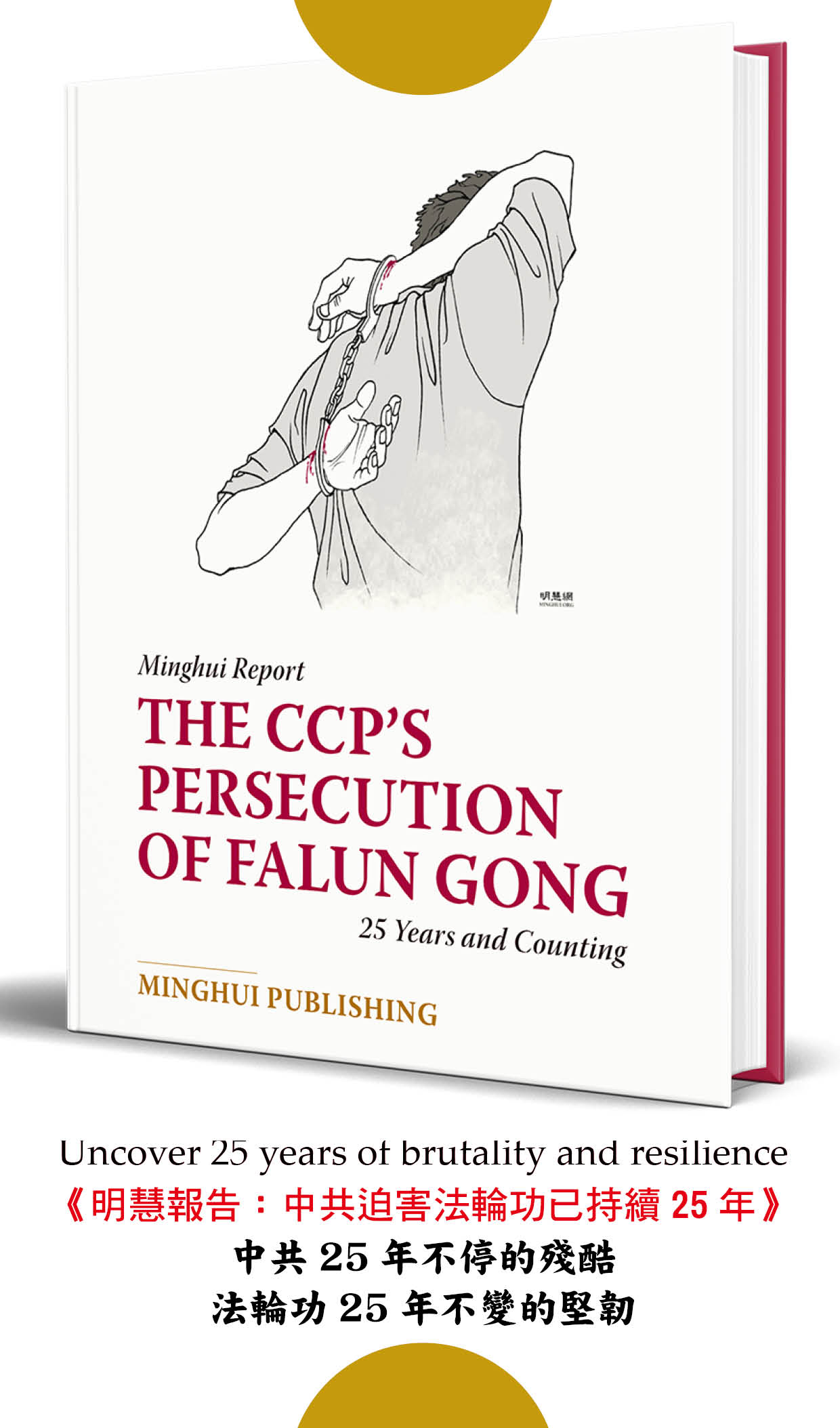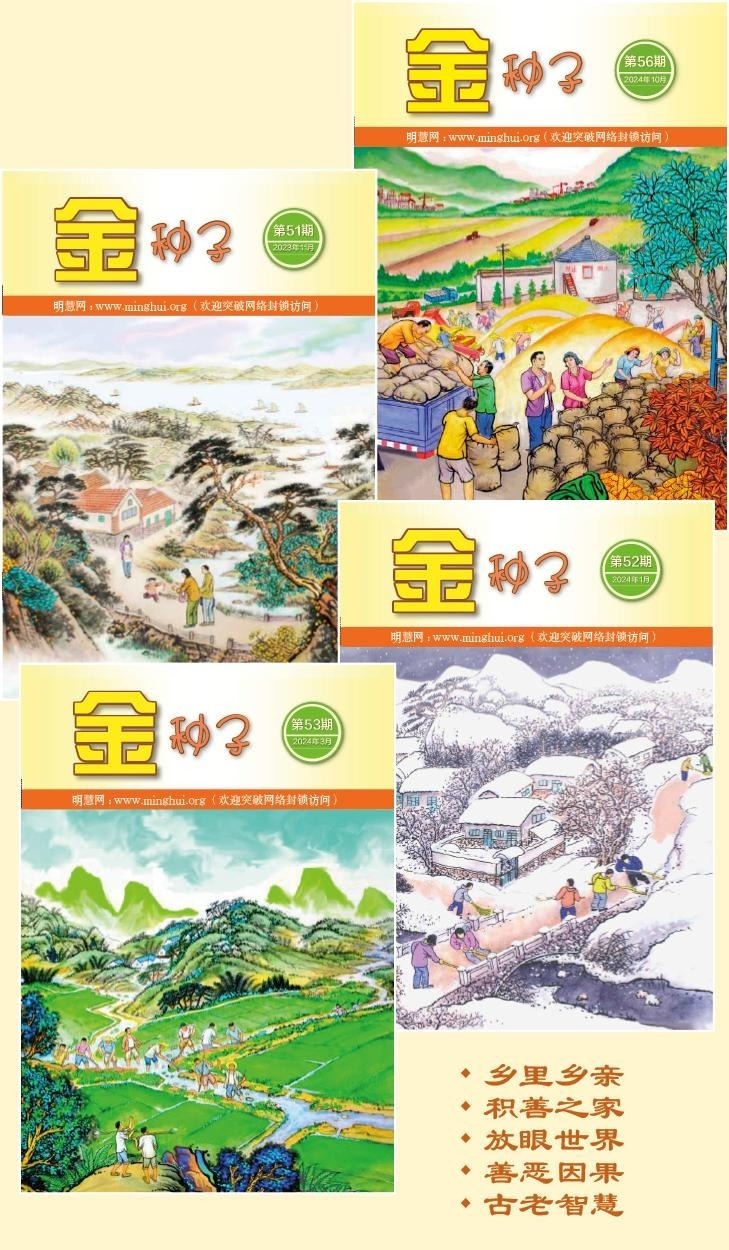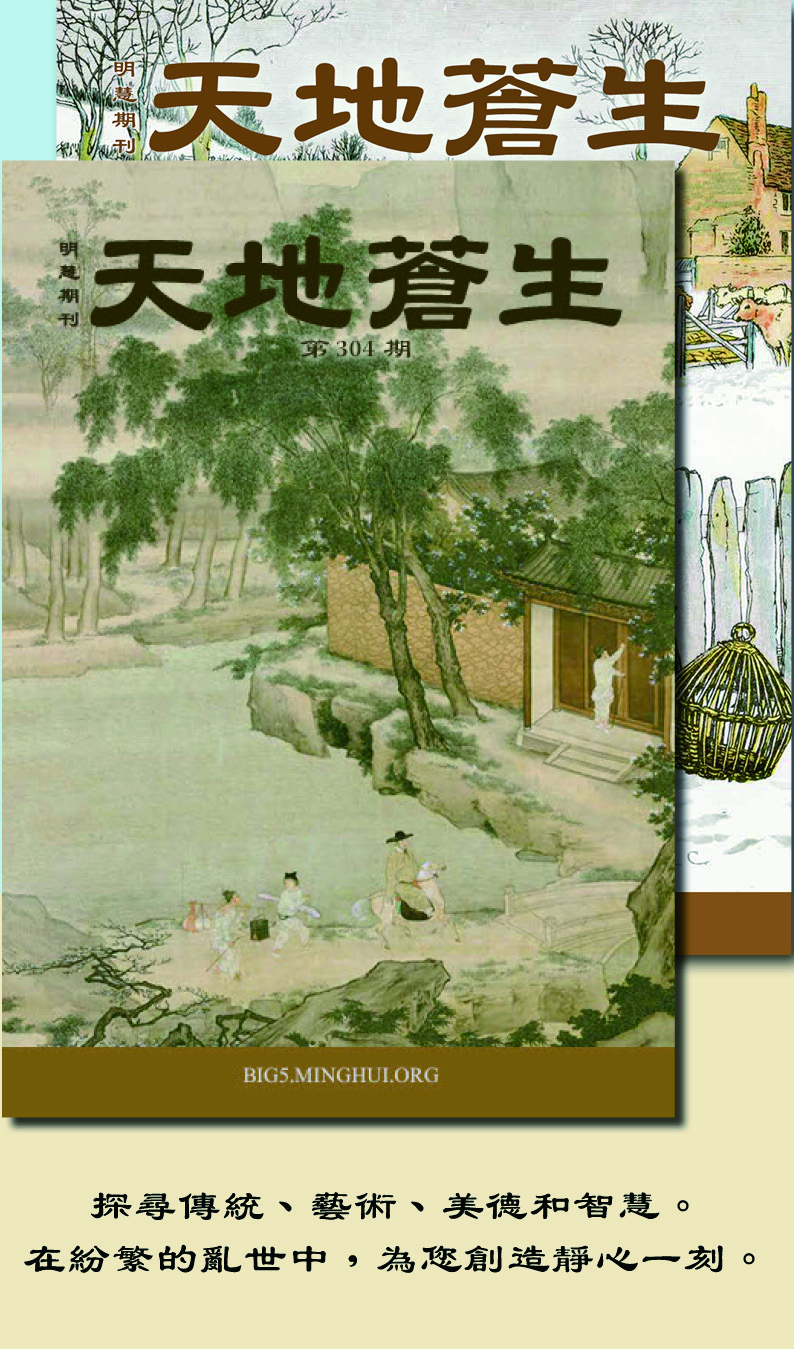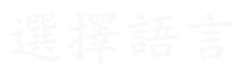怕心无存 劳教所里正念行
大法救了我的命
我十四岁才上学,一直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就是成天难受,身体瘦弱,不停的打针吃药,这边好了,那边又出状况了。到二十岁那年,感觉心慌气短,特别难受,到县医院找专家用仪器检查,检查完大夫光看着我不说话,我就问是啥病吃啥药,他说,唉,吃什么药也起不了大作用,你年轻轻的,怎么是这个病。我问是啥病?他说:“是先天性心脏病,吃什么药都起不了大作用,你的心脏就好比是个苹果,已经坏了,你想叫这部份坏的通过打针吃药好,不可能。你只有少生气,少干活,多吃点好东西,这样能维持着不向坏的方向发展就算不错了,你吃什么药都是白花钱。”
当时我想,自己没有一个好身体,也不能连累别人。所以这事也没对任何人讲,感觉生死对我来说无所谓,根本也不怕死,以后省得给别人造成负担。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们村有炼法轮功的,我母亲就听别人说这功很好,也不要钱,叫人做好人,听说很多有病的人通过炼功都好了。我什么功都没炼过,也没问过气功是怎么回事,心想炼功点就在家门口,也不要钱,就试试吧。
我第一次去炼功,感觉很好,四套功法炼完后,身体非常轻松,也非常舒服。从那以后我就每天坚持学法炼功,从不间断。按照师尊要求的用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身体一天天的好转,精神也充实了,以前那种成天打针吃药,无精打采,遇事就烦,病魔缠身的现象不翼而飞。
炼功前,因为我不能干重活,还得经常花钱吃药,家庭贫穷,夫妻之间经常吵架,感情不和。而修炼大法后,通过学法、炼功、向内找,我的家庭也和睦了,亲朋好友关系溶洽了,经济也宽裕起来,一切都和顺了。
做好人却屡遭绑架
九九年七月,江罗集团利用个人职权凌驾在法律之上,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栽赃陷害、污蔑关押,无所不用其极。我于二零零零年去北京上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后,遭到恶警的打骂、电击,后巨野县“六一零”将我非法关押一百四十六天,向家属勒索几千元钱,才放人。从此,经常有公安局和乡派出所的恶警上门骚扰,多次非法抄家,家里人一看到穿警服的就吓的心惊胆战。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我第二次被恶警绑架、非法抄家,在公安局被折磨一个晚上,又在单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四月十五日,恶警将我强行绑架到山东王村劳教所七大队。
在劳教所反迫害
王村劳教所的七大队和八大队,主要非法关押大法弟子。我一被关入监号,恶警马上安排两个犹大昼夜监控我,寸步不离,不许我跟别人打招呼,更不准交谈,恶警、犹大轮流向我灌输污蔑大法的言论,企图逼迫我放弃信仰。几天后看我不动心,就开始肉体迫害,如面壁罚站,两手下垂,不许说话,犹大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恶警更是拳脚相加。
两个星期后,恶徒看我仍不放弃信仰,就把我关到严管班,昼夜不停精神折磨,开始还让每天睡五小时,到五月份,一天只让睡一个小时的觉,凌晨四点睡、五点起,持续了二十多天,几个人轮班熬我们,逼我们脸对着墙壁罚站,恶徒拳打脚踢。但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法,都改变不了我们信师、信法这颗坚定的心。
后来我想,不能再接受他们的无理迫害,恶警及犹大背后是受旧势力及邪恶的灵体所控制而对我们大法弟子加重迫害的,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认可,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要讲真相,坚持正信,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迫害,我也不怕他们对我的任何迫害。从绑架那天起我也没有任何怕心。我要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先天本性的一面,也同时清除解体他背后邪恶的一面。
有一天,犹大王某写月小结,叫我面壁思过,我说:我没什么错,思什么过呀。我不配合他,他就动手强迫我面壁,我大声和他讲理,制止他这种邪恶行为,告诉他这样做是违法的。这时劳教所的大队长、教导员来了,我不怕,继续和他讲理,他们看着我笑笑就走了。这时犹大也不敢再那么邪恶了,我睡觉的时间也提前了,从早上四、五点改为夜里十二点。
在严管班里,恶警对法轮功学员不但在肉体上折磨,每天除睡觉、去厕所和洗刷外,都得在小板凳上坐十七至十八个小时,头和胸都要挺起来,双膝靠拢,两手放在膝盖上。否则就要挨打受骂,达不到标准就加点加重迫害。出门去洗手间都得大声打报告,声音小点,都得拉过来重打,再不行还得重来。去洗手间只能中午去一次,其它时间不让去,规定大便三分钟,小便一分钟。特别是我去洗手间,都有值班的跟着,解大便的时候两分钟不到就从茅坑往外拉,有时候用烟喷,有时候用水浇,解大小便很少让洗手。总之每次去厕所都要遭到凌辱。
恶警在精神上也给我们施加压力,经常强制让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相。我们几个人不看,把脸转向背后,他们叫我们转过来,我们不听那一套,恶警就强制我们转过来,我们不转,恶警就强制我们罚站,放多长时间录相,叫我们站多长时间。
有一天又放邪恶录相,我们在后排坐的三个人都到里屋去坐,别人一看我们走了,他们也都走了,值班的大班长就找来了警察,问谁先走的,值班的说是我把他们带走的,警察说:算啦,都不愿意看就别放啦。
我想他们怎样对我,我也无怨无恨。我就要正一切不正的,决不听邪恶的安排。他们叫我站我就坐,叫我坐我就站起来。值班的这些人在恶党警察的指使下,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我就大声不停的喊:“真、善、忍大法不允许你们打人骂人,你们打人骂人是违法的。”有时候我就走出门在走廊里喊。我被监禁在六号室,烟味、风油精味太大,我想这是警察强加的,我还是回七号室,警察不让,说我回去严管班不稳定,从此我就绝食不吃饭,一个星期后,警察队长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这屋里气味太大,他说可以在走廊里吃。他给值班的说:你们谁也不能在这屋里吸烟,想吸就到厕所里吸去,风油精谁也不能再抹。就这样我在值班室里坐,在走廊里吃,在七号室睡。
有一天早晨天不明,值班的就叫我到外面去坐,并且张口就骂,我说你值班也不能随便骂人,他说骂你怎么啦,我说你骂我就不出去,他就强行往外拉,把我的上衣都拽烂了,也没有拉出去,我就大声和他讲理,警察来了,看了看也没说什么就走了。我说你为什么骂我,为什么把我的衣服拽烂。后来他觉得自己不对,就拿了自己的一件好褂子赔我,我说:我不要你的衣服,我就是不许你迫害我。
记录被迫害的同修
有一天,严管班放诽谤大法的录相,有些同修不看,警察大队长教导员打骂一姓刘的同修。这位同修不接受他们的迫害,给他们辩理,恶警就叫来几个值班人员把他拖到办公室,抬来一箱子电棍,把他吊铐起来,轮番电他,又使用其它刑具对这位同修迫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又将这位同修拖到下边小号里迫害,两个警察和两个值班的轮班看管,警察住外面的套间,里面的小屋又脏又臭,有人在里面随便大小便也没有人管。我记得当时是七、八月份,是蚊蝇最多的季节,这位同修被拖走时穿的是短衣短裤。在里面整天被双手铐着,也动不了,蝇子吸,蚊子咬,不吃不喝,嘴上干的都流血了,给值班的要点卫生纸都不给。一般的人坐上一星期就过去了,一个星期后他还不配合,又延长到十天,最后把他关到六大队继续迫害。
和我被关在同一号室的一位同修家是潍坊昌邑的,刚来时被恶警用电棍击伤了腰部,腰直不起来,黑白天都在床上。有一天他要去洗手间解大便,几次要求,值班的就是不让去,两个人把着门不让出来。结果这位同修拉了一裤子,还弄一身。当时穿的是短裤,四、五个值班的把他架到洗手间去洗,弄得走廊里都是粪便。零七年这位同修被转到其他大队加重迫害。
八月份,警察又对我们强制“转化”。我想所谓的做“转化”的人,有的是跟大法结了缘的,由于承受不了压力,做了背离大法的事。通过跟他们多次交流、切磋,他们归正了自己,有的写了声明,有的因此被恶警严管,有的被强迫劳动,只有个别怕心重的不敢说话、不表态。
有一次,一个刚被绑架来的同修走入误区,被警察利用来“转化”我。我严肃的告诉他:“你自己走的路你都不知道,还说帮助别人。”他没有吱声,三天后这位同修醒悟了,写了严正声明,被恶警拉到办公室加重迫害,把他背铐着坐在地上,前边把脚垫起来,用力狠压膝盖,疼的直叫,眼睛一直流泪,残酷迫害了几天后,被关到严管班。
遭暴力灌食
九月份的一天,警察安排两个邪悟的人向我散布诽谤大法和师父的言论,恶警李公明从外面窗户往里看我们,问他们我有没有认识,他们回答没认识,李公明说:没认识明天参加劳动去算啦,别做工作啦。我说我不参加劳动。他一听大为恼怒,走过来对我拳打脚踢,向我胸部猛击,又左右两个耳光,恶言恶语的说:不转化,不劳动,要加倍整你。
十月十五日,两个值班的恶人向我脸上吐烟圈,还恶言恶语骂我,我善意规劝一直不听,恶警王新江和宋南叫来了四、五个打手,把我抬起来,我不停的喊“真、善、忍大法不准你们迫害我。”他们把我抬到会议室,按倒在地上,有的猛压我的大腿,有的用力压在我身上,有的在我头上身上拳打脚踢,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叫田龙云,两手捂住我的嘴用手指猛捏,当时我的牙齿被他捏掉一颗,捏歪倒四颗,满嘴流血;当时恶警王新江、宋南在一旁监督。
由于牙齿被捏的歪倒,不能吃饭,十天后他们要给我灌食,遭到拒绝后,就强行抬我去卫生所,按在椅子上,两只手背铐,两只脚别在椅子里,两边各有一个人用脚蹬住,后边一个姓王的恶人脚踩住手铐用力一蹬,我疼的大叫。我说:你们再迫害我就告你们,我不能灌食,我的牙被你们打动啦。负责灌食的卫生所长要看我的牙,我不张嘴,后边的人拽我的头发,两边的人捏我的嘴,灌食的看到了,不敢下胃管强灌了,就拽头发捏嘴从嘴里灌。从那以后到走出劳教所的这半年期间,我只能早晨喝一勺玉米面水,中午吃一勺菜,晚上一勺菜。
零六年除夕晚上点名,由于抗议恶警长时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和纵容恶人干扰迫害,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没有应声,恶警李公明大为恼火,拿着硬纸板做的点名册的尖角在我脸上不停的四处乱磕乱砸,还恶言恶语的乱骂,什么难听骂什么,从没听过的恶语都从他嘴里出来了。
不承认迫害
零七年,王新江当副大队长后,把我们硬关到一间小房,一天到晚不见太阳,白天还得睡几个值班的,晚上十几个人睡在里面,气味非常大。白天我们坐在不到一米宽的过道里,要我们都回头朝里坐,我就是不朝里坐,我朝外面坐,在门口,看到王新江我就要求他给我们调离地方。有时出门在走廊里给他讲,王新江很少在严管班停留,以后我看到警察大队长、教导员,还是劳教所里的什么人,还是省里的什么人,我都要跟他们讲道理,说明事实真相,要求调换地方。后来他们允许我去晒太阳,也允许我到以前的床上去睡,我说光叫我自己晒太阳还不行,他们也得需要去晒太阳,我们都得搬过去才行。
有一次在会议室里,警察队长半开玩笑的说:哟,你现在高级了,队长的高高凳子你也敢坐。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对社会、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我什么时候也不低级。
有一天,恶人又在打骂我,我正面制止他,警察就叫我去另一号室,里面有一个刚绑架来的淄川的同修,用两个大型铐子打着背铐,铐在椅子上,下着胃管,一头用胶带粘在头上。这位同修已经在当地看守所绝食十三天,又被绑架到王村劳教所。两个犹大在屋里干着活,监视着这位同修。这时同修说要小便,两个包夹漫不经心的说队长不在这里我们也不当家啊。这时这位同修又大声的说我要小便,把头用力一甩,把下的胃管甩出来啦。我说:你们不当家,可以去找队长,队长叫不叫去,没你们的责任。不一会包夹去找警察好久才回来。这时恶警王新江来了,看了看那位同修,又看了看我,气急败坏的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是队长叫我在这里的。他赶我回去,我不听他的,他抓着我就往外拉。别看他一身肉,就是拉不动我,他又叫了两个包夹往外拉我,到了铁门口时,我抓住铁门就是不动,王新江恶狠狠的用拳头猛砸我抓铁门的手,又用脚猛往门里跺,拽到五号监室,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还往我脸上掴耳光,打的鼻子、嘴都出血了,满脸都是血,身上也是血,躺在那里好长时间没能起来,王新江叫来犹大大班长,让他用湿毛巾把我脸上的血和衣服上的血擦了,叫他看着我,我迷迷糊糊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恶警是如何迫害的那位同修,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把我抬回到严管班。
一连几天我绝食不吃不喝,警察大队长去找我,说你有什么事尽管说,该说的就说,该吃的也得吃。我说有事找队长算不上什么错,你想那位学员不吃饭你们强给他灌食,灌到肚里不让他大小便那能行吗?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信仰是我们的自由,你们不能那样铐着迫害他,我说的也不算多,王新江就那样打我骂我迫害我,我也不怕他打,我也不怕他骂,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警察大队长只好说,他这样做是他的不对,叫他给你赔礼道歉。第二天王新江来了,他说,前几天是我的不对,我不该打你骂你,以后保证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怨,也没有什么恨,你这样打人骂人是对你自己不好,再说你们当警察的也不能随便打骂人吧?!
绝食七天后,他们又采取了另一种迫害方式。知道我不同意灌食,就把我绑架到三五八医院强行查体,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把我的一只手铐在床头上,另一只手叫包夹按着,一瓶一瓶的打了一天吊瓶,都是不明药物。我说坚决不打了,医生说你不吃就得打,你不打把脚手都铐上也得打,你吃就不打了。到晚上我想,我虽说几个月没吃主食了,七天不吃不喝也好,十天不吃不喝也好,一点也不感觉饿,精力非常充沛,身体气力也很好,虽然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从没感觉困过。劳教所里很少有机会洗澡,偶尔允许洗一次,一年四季都是洗凉水澡,每次叫洗时我都洗,就是三九严寒从不间断。我一个好的身体,不能被他们残酷的迫害,他们说打的是营养药,实际上这种药对我的身体破坏力极大,到了第三天就感觉四肢无力,筋疲力尽,肉象刀割一样的疼。我想我得早点离开这鬼地方,不能再让他们迫害我。我说我就是不在这里,我坚决不吃,爱怎么样怎么样,下午就把我拉回劳教所。
邪恶的“转化”
恶警将关我关在会议室里时,我曾经记录下劳教局关于警察执法的部份规定,一张是七不准,一张是十不要:一、不准直接参加和指使、默许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劳教人员;三、不许索要、收受、侵占劳教人员及其家属的财物;六、不许克扣、挪用、侵占劳教人员伙食费和其它财物;九、不许违反规定对劳教人员使用禁闭和警械具。不许劳教人员管理劳教人员代行警察职权。他们做的恰恰相反,去掉上面的“不准”、“不许”才是他们的真正行为。那些规定只是挂给外人看的。不准劳教人员代行警察职权,却总是由社会上其他行为的劳教人员看管大法弟子;总是指使、在一边看着那些人毒打折磨大法弟子;对不放弃信仰的大法弟子关小号、用刑具更是家常便饭。零六年全国迫害法轮功总结会在王村劳教所召开,恶警李公明曾大言不惭的说:主要是想听听我们做“转化”工作的经验,一个是多学习,一个是加期,一个是采取措施,一个是严密管理。
说白了,多学习就是高压强制听他们灌输邪恶言论;加期就是针对有些大法学员的人心,以加期或无期相威胁使被迫害者看不到希望;采取措施就是用时时可能来临的肉体折磨加重大法学员的恐惧心;严密管理就是严格隔绝大法学员之间的任何交流,不仅是语言,甚至连递个眼神都不行,在难耐的寂寞和可怕的恐惧中导致人心重的学员精神崩溃,落入他们的圈套,做了大法学员不应该做的事。零六年上半年,全所十几个大队共有十个人被非法加期,其中非法关押在七大队的大法弟子就有九人,都是坚定信仰不“转化”的。加期有半年的,有三个月的,最短的是一个月,加期的理由仅仅是在一次所谓的法规考试中,有关诽谤大法的题目没答全,有的写名没答题,有的答题没写名,有的没写名也没答题。有个同修仅仅是在纸上写了几个单个的字,清身时被搜走,就给这个同修加了一个月的期。恶警对这些大法弟子都是白天强迫劳动,晚上不让睡觉,逼着听他们讲攻击大法的言论。后来这些同修都被转到其它生产大队加重迫害。
闯出劳教所
有一次,我见到警察教导员就问他,不准克扣、挪用在所人员财物,为什么扣我的现金,李公明说你签字了吗?我说管财务的要扣我的伙食费和医药费,我没什么病,你们强行给我打针,药费我不接受,我也不签字。他说你在这里什么也不写,一年给你加一个月的期。我说我没期,我也不接受加期。
有一天,恶警李公明要赶我回严管班,我说我不走,前几天你说好的叫我在这里就行,今天为什么赶我走,你想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不行。到了下午,李公明叫来了几个打手把我抬到严管班,放在床上,我说我就不在这里,我也没什么怕心,我就不接受你的迫害。我起身想走,刚下床一头栽在地上,待了段时间,有人问李公明怎么办,他说再把他架到会议室里去吧,就这样又把我抬回来啦。
有一天,警察大队长说你快走了,一个月给你加一天,加十二天。我说:我从没想过这事,我没犯法,也没犯罪,我一天也不该待在这里,是当地“六一零”加的罪名,二零零零年我去北京上访,非法监禁一百四十六天,勒索钱财几千元,几年了也不还,还变本加厉的迫害好人,天理不容。
零七年三月十七号,也就是我被绑架后的第一年零三天,恶警宋南看我不吃饭,又一次把我拖到医院迫害。第二天上午王新江和管账的警察匆匆忙忙到医院叫医生拔了吊瓶,叫包夹把带来的东西全部带走。我刚走出门王新江非要给我戴铐子,我说:我都被你们迫害成这样啦,还给我戴铐子,我不带。就这样他们又把我拖到劳教所,按在床上,当时屋里有好几个人,有警察、包夹,还有不认识的人,恶警李公明指挥,他们做着各种姿势在我旁边对着我录相,我也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主意,也可能是怕以后出了什么事,推卸责任,搞假证据吧。
离开劳教所的时候,李公明和管账的警察还有包夹把我从关押了近一年的大楼里送出来,结账时还是把医药费扣了,当时我说:我不在乎钱,我就要正一切不正的,教导员说过不签字不算数,为什么扣我的现金。管账的问李公明:你当时说没说这话。他说当时说过。管账的说那就不能扣人家的,又从新结算。
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家里人多次去看我,劳教所都不让见面,后来听出来的同修说了我的情况,家里人急了,去找当地“六一零”,他们怕担责任,给开了信,才让见了一次面。我给家里人说这里的事你们就别管了,是当地“六一零”把我送这里的,什么事都有他们负责。我回家的那天,“六一零”推卸责任不去接,最后还是家属接的。这一天是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这一次我被非法监禁、受迫害共一年零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