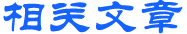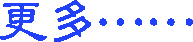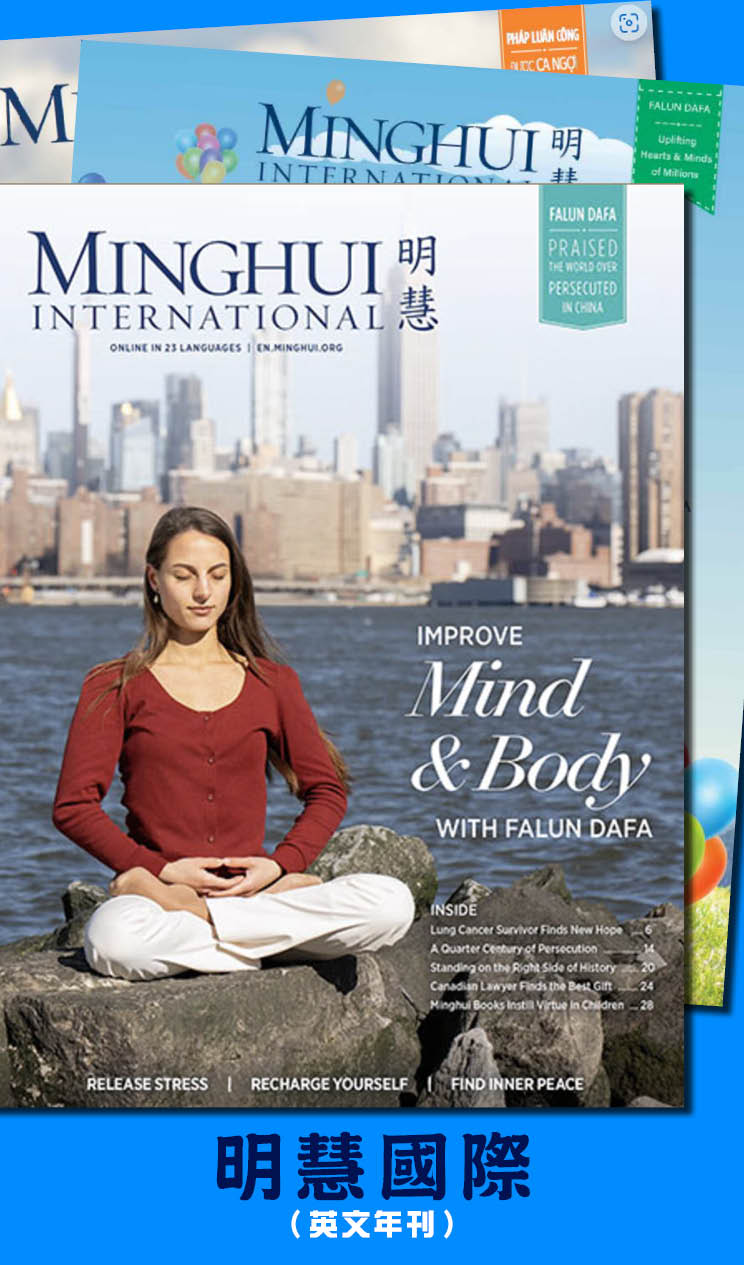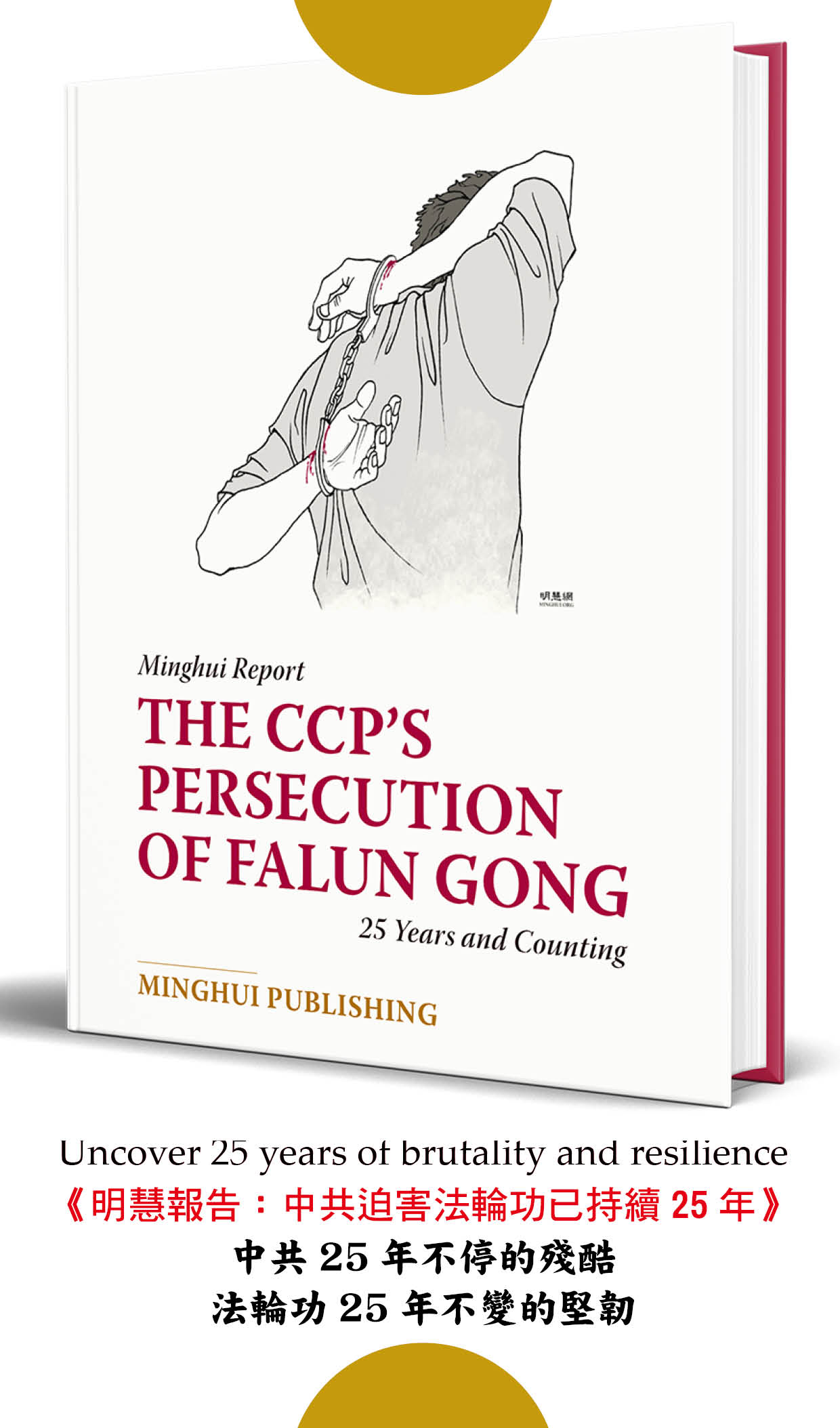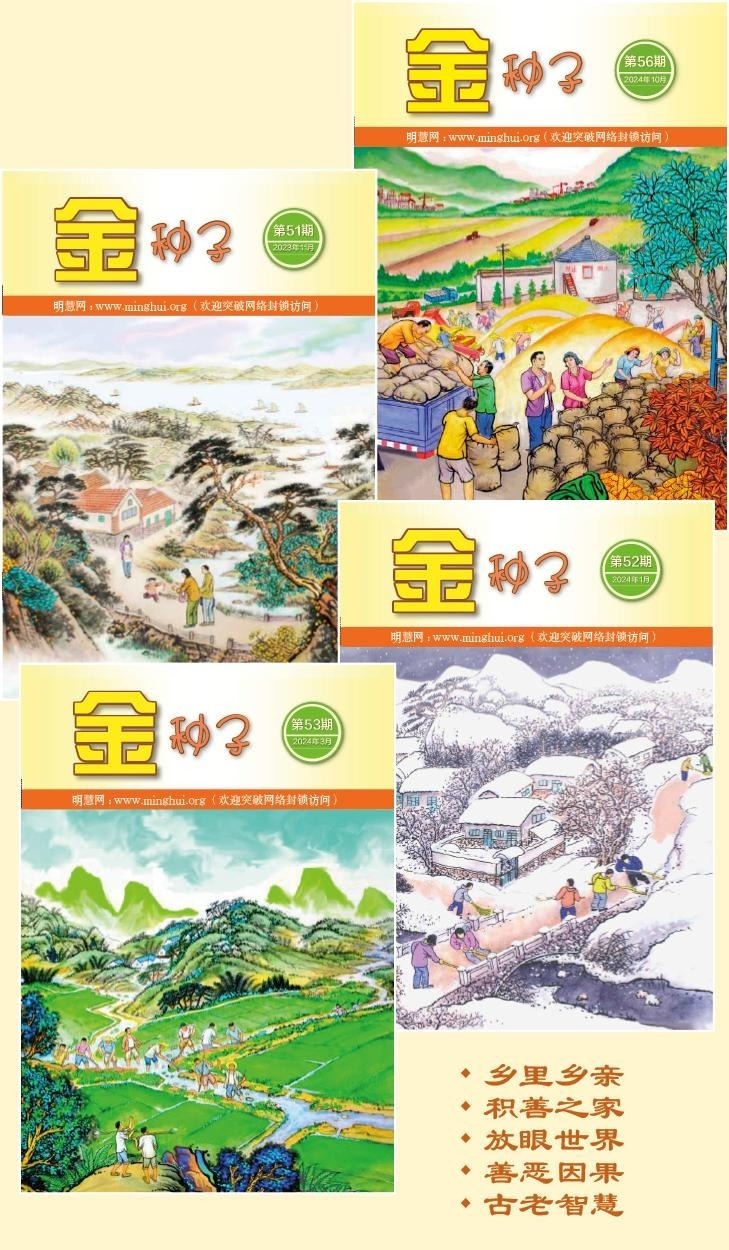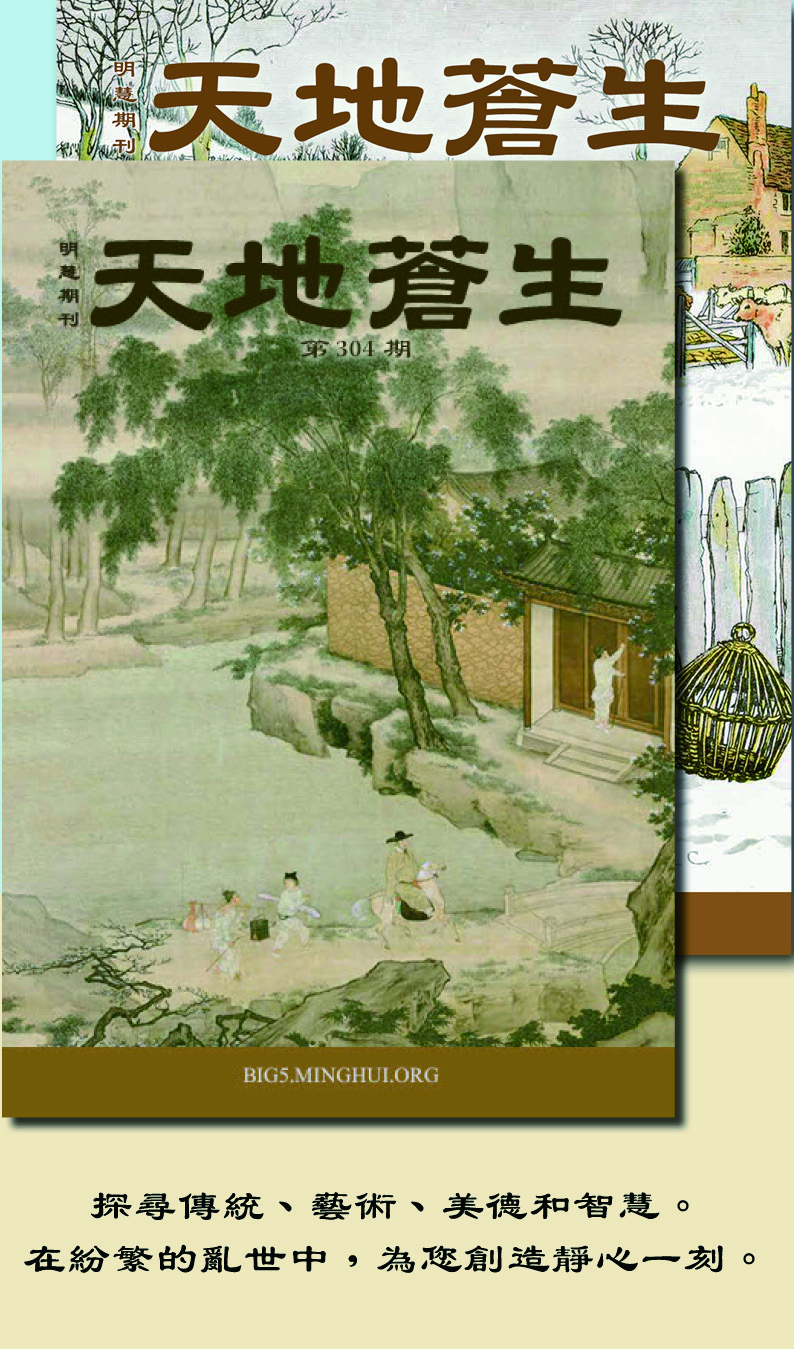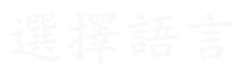青年学生的修炼故事
97年大学二年级,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那时我只有一件事放不下心,就是父母几十年多种疾病缠身,个中痛苦一言难尽,也是这个幸福家庭唯一的缺憾。98年7月,放暑假回家,准备在家呆三天后与同学去北京上一个出国留学考试的辅导班。在家的三天时间虽短,却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那天我考完试赶回家,妈妈便递来一本书,说是她路过公园时,看见有人在炼一种从未见过的气功,产生了兴趣,一位不相识的炼功人便把这本书送给了她。妈妈说那几天她有些头晕,读不了书,让我给她念念,我当然愿意,接过书一看,封面上三个大字:“转法轮”。在那之后的三天里,我一有空就给妈妈读《转法轮》,一边读一边叹道:“有道理,有道理。”其实现在想来,那时我觉得有道理的大部份原因,是因为妈妈是个急性子,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火,我想,如果她能修修“忍”,一家人也就自在了。父亲是个坚决的无神论者,只说:“教人向善我接受,可太玄乎了。”三天后,我已为妈妈念完了大半本书,启程去了北京。
一个月的课程将近结束时,我打电话回家,妈妈在电话里只告诉我尽快回家学炼法轮功,她说:“奇迹发生了,你爸爸和我的病全好了。”我非常吃惊,因为父母是远近出了名的药罐子,和医院打了几十年交道,求助于各种功法却都是徒劳。而炼法轮功才不到一个月,各种病症全部消失,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连原本不信的父亲也大为感叹。但是我仍有些疑虑,心想,该不是他们的心理作用吧!我赶回家中,事实让我心服口服。然而,我却打不起炼功的精神,想想自己是学校的运动健将,用不着炼什么气功。
在和功友们交流并读了一些学员的心得体会后,我才惊奇地发现学生、教授炼法轮功的还不少。可我由于学法不深,还惦记着暑假有很多其他事要完成,哪来的时间炼功。但碍于很久没好好陪父母了,便随他们到公园里试着炼炼。没想第二套抱轮刚开始,我突然浑身一阵虚软,接着冷汗如雨下,眼前一黑,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也许是受之前所听闻的学员消病业心得的鼓舞,我不知怎的脑中清楚地冒出一个念头:我是法轮功弟子,我一定不会倒下!这个想法让我自己都吃惊,因为那时我还没打定主意是否真正炼法轮功。然而就在那正念出来的瞬间,我看见眼前出现了一个飞速旋转的银色风扇般的东西,我以为是幻觉,眨了几次眼睛,却见它依然在那儿,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看得非常清楚。同时,身体似乎被一股什么力量支撑着。就这样,我硬是把抱轮坚持下来了,并没有晕倒,冷汗湿透了衣服甚至鞋袜,而我却感到一身轻松。事后问老学员,才知道那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我看见的是法轮。我这才从过度的自信中清醒过来,明白自己身体里的隐患不知有多少,从那以后,我的体力不断地增强。
从小到大我从未想过自己和修炼能扯上什么关系,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也觉得自己是个有思想、不盲从潮流的人,更以为自己心性不错,也能吃身体上的苦。可读了大法的书并和学员交流后,我才发现自己离法的要求远去了,同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我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从此走上修炼的路,但却要能吃苦,因为放下名利情于我而言并不容易;另一个是安安稳稳地过自己习惯了的日子,活在别人的喝彩与自己美梦里。师父说:“人就执著于这些东西,你说你能静得下来吗?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象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尽管在初期的学法与交流中我明白了放弃执著心并不等于在物质上真正放弃什么,可一想要面对的是更高的要求、更高的考验,我不禁在心里叫苦。做出决定修炼与否的那几天里,我一直在思想中痛苦地挣扎徘徊,那是一次理智与情感的斗争,思想业力极力阻碍,可明白的一面毕竟是主导。终于,我对父母说:“我决定修炼。”那一刻我前所未有地轻松。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机缘,只深深地感受到在那以后的一路前行中,法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如此美妙,如此殊胜,我庆幸自己没有因一念之差而与这万古机缘擦肩而过。我告诫自己,也真心希望有缘的人们,理智地看待生命,珍惜自己的善念。
我们一家修炼之后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很惊讶。尤其是妈妈,原来是有名的急性子,加上身体不好,常对家人和亲戚大发脾气,闹得亲戚都敬而远之。学大法后,妈妈身体好了,几十年的坏脾气也渐渐地好了。在刚学法几个月时,有一天晚上,妈妈没忍住对我发了脾气,事后她知道自己没做好,关起房门学法去了。第二天早上炼完功,妈妈对我说:“对不起,妈妈错了,不该发脾气。”在一旁听着的父亲差点没掉下泪来,感慨地对我说:“几十年来,你妈妈从没承认过自己有什么错,从没说过一句对不起。”目睹我们一家身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亲友、同学也捧起了《转法轮》。
作为一个学生,在十几年的学校生活中形成了成绩、名次至上的观念。我一向成绩不错,又是学生干部,似乎没什么可和别人争的,也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心态好,不怎么看重分数。学法以后,争斗心、虚荣心才暴露无遗。在开始学法不到两个月时,也就是大学四年级,班里排名次。开始我得知自己在全班一百一十多人中排名第八,心满意足,觉得自己心态好,不求第一第二。后来由于我在两份学术期刊和一份报刊上共发表三篇专业论文而加分,成了全班第一名,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看着其他同学为了加一分两分而绞尽脑汁、勾心斗角,我还自以为做到了“无所求而自得”。可紧接着,我发现有规定,在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加分不同,报纸上发表的加分少一些,而我先前的总分是按三篇论文都在期刊上发表而计算出来的,那就意味着我的分数应该倒扣一些,这样一来我可能就不是第一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那时候第一名对我来说,无论是对出国留学的申请还是对留在国内找工作,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开始我不愿正视可能失去好不容易到手的第一名这一事实,心想那么一点小细节,没有别人会注意到。可马上发现自己那一念错了,我是个炼功人,应该用更高的理要求自己。于是我给辅导老师留了个条,希望她能从我的分数中扣去不该加的部份。一周后,辅导老师对我说:“分数给你扣了,可你的总分很高,仍然是全班第一名。”我看得出她的惊讶,因为那一段时间找她的学生络绎不绝,都是争着吵着要加分的,而唯有我是主动要求扣分的学生。
去年4.25之后,一位功友对我说,他随时准备被派出所带走。我听了没往心里去,觉得事情不至于这么严重。我生长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中,从小家庭学校就教育我要遵纪守法、做个好公民,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从未想过和派出所、公安局有什么打交道的机会,学了法轮大法更是严于律己、做更好的人,怎么也想不出公安局有什么理由会抓好人。可是事非己料,当周围的功友开始被抓、被跟踪,各单位开始清查、开除学员时,当家里电话开始被监听时,我才意识到考验就在眼前。
那时我还没毕业,结业证、学士证都还没发下来。我是个党员,也是我们系几十人的学生党支部里唯一的法轮功学员。周围的紧张气氛在我心中被演化得更为严峻: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有可能因证件办理手续被卡而出不了国。不修炼的哥哥劝我别给自己找麻烦,而我的怕心则是在不断学法、不断磨炼中渐渐去掉的。我想,我明白大法是好的,自己为什么就没勇气站出来说句真话呢?于是我抓紧一切机会向周围的同学、朋友洪法,讲述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时媒体尚未展开大规模的污蔑,我只希望更多人能知道真相。当时,有通知说,我所在的学生党支部因临近毕业,不再开会了。我不禁欢喜心起:是不是因为我这一关过得不错,不用再考验了?可不过一天,又来通知说当晚补开最后一次支部会议。师父在经文《挖根》说:“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掩蔽很深的心,去掉它。”身临其境时我的执著暴露无遗,一瞬间什么念头都上来了。如果这次开会是为了批法轮功,我该如何做?一旦挨处分、被开除,甚至进派出所,十几年的苦读和长期的出国准备没了下文,等等等等。我甚至想到了要请假逃避。然而想想自己是个炼功人,我开始嘲笑自己的懦弱:为什么明白了真理与正义所在还不敢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呢?如果昧着良心欺骗世人,我又对得起谁呢?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说的人,一个连自己的良心都能出卖的人,哪怕在常人的专业领域中有再高的造就,又何以配得起社会的重托与期望?我决定如果会议上讨论法轮功问题,我一定会站出来以真心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为了不使大法书籍被抄被毁,当天我就把宿舍里所有的大法书籍和录音带转移走了。之后,我坐在书桌前开始写日记,从自己和家人为何修大法、如何受益写起。我想,即便宿舍被抄,也希望这篇日记能唤起有缘人的一丝善念,明白大法是好的。那也是一篇自己几个月修炼的总结,在写的过程中,我更清晰、更理性地正视自己的执著,也更体会到法的洪大与师父的慈悲,我不禁泪下。收拾妥当后,我赶去开会。那晚的会议,对法轮功只字未提,之后不长的一段日子里,我毕了业,拿到了来美国的签证。
七月二十二日,几乎所有电视频道都在播放攻击大法的节目。我和父母一边看一边哑然失笑:堂堂的国家电视台,居然能播出如此歪曲事实的报导。从小我就接受爱国教育,天真地相信一切来自政府的报导。尽管很多人对我说媒体有许多报导是不实的,我仍用一颗明朗的心看待着这个社会。然而政府舆论对大法的攻击彻底地击碎了我的信任。我十分伤心,为什么政府要说假话?那我从小到大所相信的言论又有多少是真的?那时离我出国只有三天了,我准备也和功友们一样去市政府说明真相,结果被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给拦了回来。事后也知道自己那热血沸腾的状态不对,我甚至想着国内修炼环境好,要是不出国修得更快。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对法没理解好和自私的表现。师父在经文《为谁而存在》中说:“一个生命如果能真正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不带任何观念地权衡问题,那么这个人就是真的能自己主宰自己,这种清醒是智慧而不同于一般人的所谓聪明。”修炼的路毕竟不是自己安排的,七月底我离开了中国。
在国外的修炼环境似乎宽松多了,而我也面临着新的考验。由于专业原因,我的学业负担一直很重。在修炼与学习的平衡中,我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日子,我只能见缝插针地在路上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临睡前读读《转法轮》,炼功洪法都放松了。幸亏有一个和功友一起学法交流的环境,在比学比修中他们帮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我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可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是因为法没学好,心没到位,没有真正悟上来,自然也就做不好了。有一天我正赶往学校,心里突然一阵难过,不是说学校学习的压力把我怎么了,是我心里放不下的执著太重,就象肩上的书包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甚至于比这重十倍、百倍、千倍。就象习惯了日复一日如此的重荷一样,我对心里的执著也麻木了,以为修炼就是这样吃苦消业了。我是个听话的学生,教授布置什么我从是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么我又是如何做一个修炼弟子的呢?师父的话我认真地听了、做了吗?为什么教授的话一字不落地照着做,而对师父的话,却用自己层层的执著挑着自己中听的来掩盖不是真正实修的行为?有一位也在读硕士的功友说,她悟到,就象西医拔牙和中医拔牙的区别一样,有些事在常人中非得费尽周折才能做成,而用超常的理来看,不费吹灰之力。我明白我走了一条笨拙的弯路。看着周围同学们没日没夜地苦干,我是在用他们的行为在作为标准呢,还是用超常的理要求自己?认识到这点之后,我用更多的时间学法、炼功、洪法,可学习不但没落下,反而应对起来更轻松自如了。一年下来,学校对我的表现予以肯定,并授予了第二年的全年奖学金。
在摆正修炼与学习的关系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我把自己封闭在功友的圈子里,封闭在自己私心构起的框框里,用太忙了做借口,不愿和常人多交往,从而也就没把握好许多洪法机会。平时的洪法,也是因为功友们做了,我才跟着做。有时甚至还自以为洪法做得不错而自满,而这种欢喜心、显示心隐藏很深,自己都没觉察出来。是师父的点化使我看见了自己的执著。有一次我去领驾驶执照,拿回家后才发现办公人员把我的姓和名写反了,又赶回去费了一番力气才把名字改过来。我明白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没有了家族的姓氏,个人的名字何来意义,没有大法,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修炼更从何而来?姓名倒置,本末也就倒置了。我问自己,我把自己的名放到首要位置上去了吗?我能把常人间的名看淡,是否又掩藏着在大法中求名的心呢?是否做事的心太强了呢?我是真正的为了他人好还是为了自己好呢?我是真心地想使更多的有缘人了解大法,还是想让别人理解、认可自己的所做所为?师父说:“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我似乎明白了自己的执著所在,拿起《转法轮》顺手翻开,一眼就看到了师父的点化:“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我明白了我为何会封闭自己,一个“私”字蒙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见自己眼皮底那自以为是的一点理,却没真正把自己放在大法中融炼。在国内,多少功友放下生死走了出来,而我难道只有感动的份儿吗?在这样一个伟大殊胜的修炼环境中,我却没有从心里真正融汇进去,常人尚且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怎么可以因为维护着自己未去的种种执著与魔性而放任了让魔可乘的空子、给大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呢?在每一步的整体推进中,若是放松了自己,没有跟上,必然是不进则退。有什么你修得好、他修得不好的,当小小的“我”扩展为“我们”以至更大时,又有什么执著放不下呢?
封闭自我的门敞开了,自然而然地,从身边做起,洪扬大法成了我实修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教授、同学、亲人、朋友、不认识的人们,只要有可能,我都尽力通过书信、电子邮件、电话、传单资料等向他们说明真相。因为我明白,人就象一个容器,只要多装进一句真话,谎言也就少了一寸容身之地。是法的洪大,唤醒沉睡的善念,给每一个生命选择的机会。
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的话:"善与恶的表现中都充分体现了各自将要得到的结果。众生,将来的位置是你们自己选择的。"
谢谢。
(2000年华盛顿法会发言稿)